爱去小说网>地府公职处:渡厄司 > 第123章 判厄笔显异兆(第2页)
第123章 判厄笔显异兆(第2页)
她闭眼,凝神内察。默诉纹感知机制运转如常,可这一次,并无案件推进触发因果反馈。这墨痕,来得突兀,像是被什么从外面拽进来的一样。
耳边似乎有声。
极细,极远,像风吹枯井底,又像谁在梦里呢喃。
她睁眼。
笔尖那点墨痕微微晃动,如同水波倒映星碎。
“谁在拉你?”
她问笔。
当然没有回答。
但笔身热度未退,牵引之力仍在,依旧指着第七格柜门。
她缓缓起身,站定在柜前三步。
“钟暮说有人半夜来翻柜子,用的是烧毁过的判厄笔。”
她低声,“还滴了血。”
她盯着那道墨痕。
“你现在也认那种东西?还是。。。。。。它认你?”
笔不动。
她伸手,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那点墨痕。
指尖传来刺痛,像被针扎了一下。一滴血珠冒出来,落在柜门前的地砖上,瞬间被吸进去,不留痕迹。
地砖微颤。
她眯眼。
就在这时,笔身那点“丶”
突然加深一分,色泽转为暗紫,仿佛浸了血。
她心头一凛。
这不是默诉纹该有的变化。
默诉纹不会变色,不会自主生长,更不会回应外界滴血——那是仪式,不是查案。
可这支笔,正在变成她不认识的东西。
她把笔收回袖中,动作利落,却掩不住指节发紧。
“不对劲。”
她说,“这事从根上就不对劲。”
她重新看向第七格柜门。
锁是完好的,符条未断,封印如初。可刚才那一滴血被吸走,绝非自然现象。
她蹲下身,用手抹过地砖接缝。
指尖沾到一点灰白粉末。
她捻了捻,凑近鼻端。
腐香。
极淡,混在纸墨味里几乎闻不出,但确实是那种香——只有在滞影长期困锁之地才会生成的腐香,是魂体衰败时逸出的气息凝成的。
“柜子里不止关了人。”
她站起身,“还关了别的东西。”
她再次取出判厄笔。
笔身那点墨痕还在,安静下来,不再发热。
她用指腹盖住它,低声:“我不信你是冲我来的。你是冲它。”
她指向第七格。
笔无反应。
她冷笑一声:“装哑巴?行。咱们走着看。”
她转身,走向档案司西侧角落,那里立着一台老式卷宗检索机,铜盘齿轮咬合,靠魂力驱动。她将手掌贴在启动钮上,朱砂微闪,机器嗡鸣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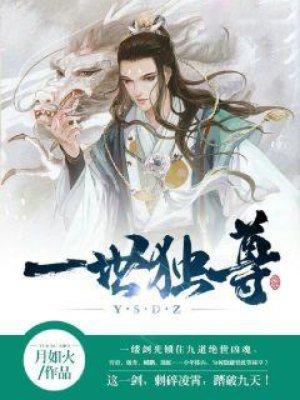
![事业脑直男,但万人迷[快穿]](/img/3471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