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去小说网>港综:洪兴四九仔,踩靓坤扎职 > 第966章 你父亲没死他只是被存档了(第1页)
第966章 你父亲没死他只是被存档了(第1页)
不是雷击,是高压电容器在断电前最后一毫秒的疯狂泄放——整条摇臂瞬间成为导体,电流顺着金属骨架狂涌而下,车内仪表盘爆出刺目火花,喇叭嘶鸣半声即哑,动机舱腾起一股焦糊白烟。
铲车猛地一滞,履带空转,出濒死般的尖啸。
塔下,阿胜踉跄后退半步,脸色煞白。
周晟鹏已跨过倒塌的围墙,靴底踩碎一片玻璃渣,径直走向基站底座配电箱。
他蹲下,撬棍插入箱盖缝隙,肩胛骨一沉,咔哒一声,箱门弹开。
里面线路整齐,灰尘极少。
唯独角落一只铅盒,表面无锁,只用焊锡封死。
他撬开盒盖,取出一枚拇指大小的微型硬盘——铝壳冰凉,边缘蚀刻四字:1994-死胎。
他掏出随身银瓶,拧开,滴一滴无色药水在接口处。
药水渗入缝隙,无声腐蚀。
三秒后,接口氧化层剥落,露出底下被强酸啃噬过的铜箔断面——可断面边缘,竟有细微液态金属凝固的纹路,像血管般蜿蜒补全电路,精密得令人窒息。
有人想毁它。
毁得彻底。
又怕毁不干净,所以用军工级液态金属二次修复——既遮掩痕迹,又留一线生机。
周晟鹏指尖摩挲着那行蚀刻字,指腹下,硬盘外壳深处,似乎还有一层更薄的夹层,在药水作用下,正微微泛起一层珍珠母贝似的虹彩。
他缓缓抬头,目光扫过阿胜汗湿的鬓角,扫过老鬼血流进耳道的狼狈,扫过周影悬在塔顶、衣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背影。
然后,他垂眸,将硬盘轻轻托在掌心。
夜风忽止。
他左手已悄然按在腰侧冷冻喷雾的阀门上——瓶身冰凉,内部压力指针正随着他呼吸的节奏,一格,一格,缓慢上升。
阿胜的瞳孔在硬盘泛起虹彩的刹那骤然收缩。
不是因为那抹转瞬即逝的珍珠母贝光泽,而是因为周晟鹏垂眸时,左手拇指已无声滑过冷冻喷雾阀柄——那动作太熟稔,熟稔得像呼吸。
十年前青龙湾码头,三名叛徒跪在货箱前求饶,周晟鹏也是这样低头,也是这样抬手,然后——咔嗒一声轻响,霜白雾气喷出,三只握枪的手腕在同一秒出脆如枯枝折断的微响。
阿胜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零下78c的液氮汽化流,能在o。3秒内冻结皮下微血管与关节软骨,使胶原纤维瞬间失韧,使骨小梁在力学冲击下呈放射状崩裂。
不是伤,是废。
废得连手术重建都省了。
他不能等。
膝盖未屈,腰腹先拧,整个人斜撞向右侧三步外堆放的锈蚀配电柜——那是他早踩过点的死角,柜门虚掩,内侧焊着一枚松动的角铁。
他扑过去的瞬间,右手已从后腰抽出一截削尖的铜管,寒光一闪,直刺周晟鹏持硬盘的左手肘弯!
快,狠,孤注一掷。
可周晟鹏没躲。
甚至没抬眼。
就在铜管距肘窝尚有七厘米时,他左腕倏然内旋——不是格挡,是迎上。
喷口正对阿胜腕动脉搏动处,阀门全开。
“嗤——!!!”
不是嘶鸣,是真空被骤然撕裂的锐啸。
一蓬霜白雾气如活物般缠上阿胜手腕,皮肤瞬间泛起死灰青白,汗毛根根竖立又蜷曲焦黑。
他整条右臂猛地一僵,指节“咯”
地错位弹开,铜管当啷坠地,而身体因前冲惯性失控前栽——
周晟鹏左手顺势一托一送,掌心贴住阿胜后颈第七椎体,借力一掀。
阿胜整个人腾空翻出,像一袋灌满水泥的麻布,朝着厂区西侧断墙后那片沉寂的阴影狠狠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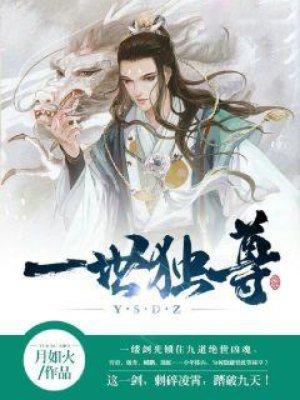
![事业脑直男,但万人迷[快穿]](/img/3471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