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去小说网>港综:洪兴四九仔,踩靓坤扎职 > 第966章 你父亲没死他只是被存档了(第2页)
第966章 你父亲没死他只是被存档了(第2页)
那里,铁头正伏在改装铲车驾驶座里,热成像瞄准镜十字线早已锁死基站底座——却在阿胜飞来的瞬间,骤然偏移半寸,死死咬住他凌空翻滚的脊背。
“打!”
铁头喉间滚出低吼。
两声闷响几乎叠在一起。
第一声是阿胜后背撞上断墙碎砖的钝响;第二声,是铁头肩扛式榴弹射器的膛口焰,在夜色里炸开一朵幽蓝火莲。
周晟鹏站在原地,未回头。
他听见了弹道破风声,也听见了阿胜落地时肋骨断裂的、湿漉漉的闷响。
他更听见了——自己腕内信标接收器,随着榴弹爆炸震波,同步跳动了一下,频率陡升o。2赫兹。
像在呼应什么。
他缓缓收回左手,指尖残留着喷雾瓶金属外壳的寒意。
目光落回掌心硬盘。
银瓶药水余效未散,接口处虹彩渐隐,露出底下更薄一层基板。
他拇指指甲沿边缘一刮,薄如蝉翼的封膜应声翘起——不是撕开,是“启封”
。
军工级生物电容感应阵列启动,硬盘自动接入他腕表内置读取端口。
屏幕亮起。
没有文件列表,没有加密提示。
只有一组生命体征图:心跳曲线平稳起伏,脑电波呈现深度睡眠的o波节律,血氧饱和度98。7%,体温36。2c……所有参数都精确得令人窒息。
监测对象栏,姓名字段静静浮现:
周振岳
——三十年前,洪兴祠堂灵位上,漆金描红、香火供奉的“先考”
。
周晟鹏的呼吸停了半拍。
不是震惊,是某种深埋骨髓的确认感,像冻土之下突然涌出温泉水,无声漫过脚踝。
他盯着那行字,指尖无意识摩挲硬盘背面蚀刻的“1994-死胎”
四字。
1994年……父亲失踪那年,母亲临盆大出血,产房传出婴儿啼哭仅三秒,便再无声息。
族谱记作“胎亡”
,祠堂未设牌位,只有一张焚尽的纸灰。
可此刻屏幕上,那颗心脏正一下,又一下,稳稳搏动着。
周晟鹏慢慢合拢五指,将硬盘攥进掌心。
金属棱角硌着皮肉,带来一丝尖锐的真实感。
他抬头,望向信号塔后方——那里,旧厂主楼地基塌陷处,一道被混凝土封死的斜坡通道,入口处焊着两道锈蚀钢门,门缝里,隐约渗出一缕极淡、极冷的白雾。
雾气不散,不升,只是静静浮在离地十公分处,像一条蛰伏的蛇。
他迈步向前,靴跟碾过玻璃渣,出细碎而清晰的声响。
每一步,都踏在三十年前那场大火熄灭后的余烬之上。
铁锈味混着液氮的冷腥,在地库入口弥漫开来。
周晟鹏一脚踹在锈蚀钢门中央——不是蛮力硬砸,而是左膝微屈、右胯后撤半寸,腰腹拧转如绞弓,靴跟自下而上斜撞门轴焊点。
轰然闷响中,门框崩裂,铰链撕开一道刺耳的金属哀鸣,整扇门向内翻倒,砸起漫天灰白冷雾。
雾未散尽,寒气已如刀割面。
地库深处,一具庞然巨物静静悬浮于幽蓝微光之中——六米高的圆柱形液氮冷冻舱,钛合金外壳布满蛛网状导热纹路,表面凝结着厚厚一层霜晶,在应急灯惨绿映照下泛出死寂的虹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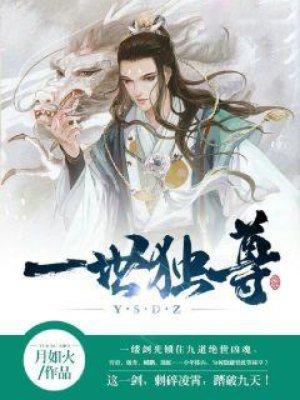
![事业脑直男,但万人迷[快穿]](/img/3471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