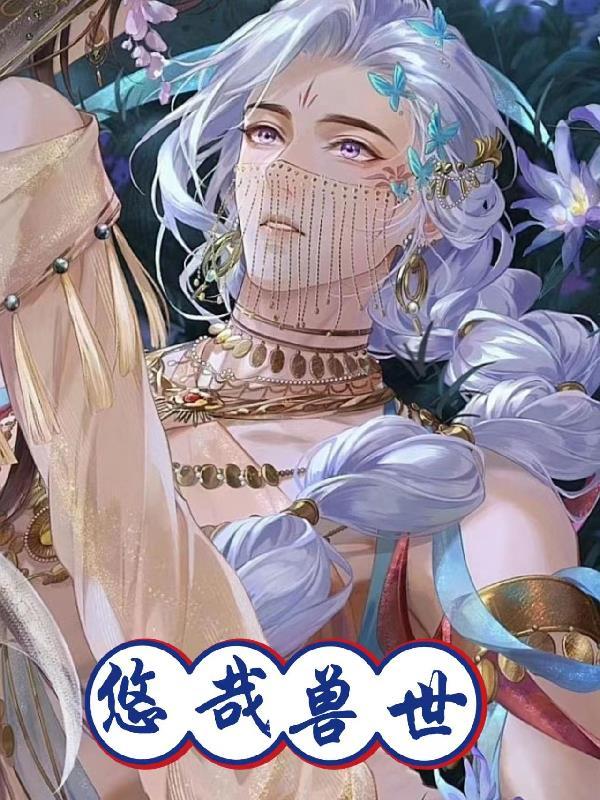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八十三章 年夜饭的预定(第3页)
第一百八十三章 年夜饭的预定(第3页)
——老周是聋哑人,昨天来定年夜饭时,用手比划着要二十个荠菜馅饺子,邢成义记在了草纸上,不知咋的没誊到账本上。“成义,去菜窖再拿点荠菜,”
她把草纸往兜里塞,“老周年轻时帮过咱素味斋盖房,可不能忘了。”
邢成义刚钻进菜窖,就听见陈露在灶房喊:“油豆腐泡不够了!张奶奶要十个福袋,现在只剩八个能装馅的!”
慌里慌张间,李萌萌举着画本进来了,画本上画着个鼓鼓囊囊的油豆腐泡,旁边写着“用豆腐皮做福袋”
。“陈露姐,我看见刘婶用豆腐皮包肉馅,”
她指着画说,“咱把豆腐皮烫软了,也能包糯米。”
陈露眼睛一亮,赶紧往锅里倒热水,豆腐皮浸在水里,慢慢变得透亮,“萌萌真是救星!这豆腐皮福袋看着更精致,就当给张奶奶家加个新菜。”
上午十点,定好年夜饭的客人开始上门取预定的素卤味。刘婶来拿卤素鸡,掀开坛子盖就皱起眉:“咋少了点八角味?”
陈露这才想起,昨儿炖卤汤时,邢成义把花椒当成八角倒进去了,现在满坛子都是麻味。“要不我给您拌点辣椒油?”
她手忙脚乱找油瓶,“能压点麻味。”
刘婶却笑着摆手:“麻点好,我那上海侄女爱吃麻辣,正合她口味。”
最棘手的是那桌“中西合璧”
的素牛排。陈露把猴头菇和杏鲍菇混着煎,浇上番茄酱时,酱汁顺着盘子缝流到桌布上,洇出片红印。“这桌客人要是介意咋办?”
她急得直擦手,手心的汗把围裙都浸湿了。王店长却蹲下来,用纸巾蘸着水慢慢擦:“咱如实说,是第一次做这菜没经验,客人要是不嫌弃,咱再送份冰糖莲子羹赔罪。”
中午时分,临时搭的小屋里突然跳闸,徐涛摆弄电闸时,不小心把保险丝烧断了,屋里顿时黑得像地窖。“用煤油灯吧,”
苏清沅从柜里翻出盏旧灯,玻璃罩上还沾着去年的灯芯灰,“老李家的父母是从乡下出来的,见了煤油灯说不定更亲切。”
果然,老李家的人来的时候,看见煤油灯在桌上跳着暖光,都笑着说:“这比城里的吊灯有年味。”
邢成义在院里摆碗筷,摆到第三桌时,现少了两双筷子——早上还数着够数,许是被来串门的孩子揣走了。“我去张奶奶家借,”
他往巷口跑,张奶奶正坐在炕头纳鞋底,听见要借筷子,掀开柜盖就往外掏,“这是我备着的新筷子,红漆的,过年用正好。”
筷子上还缠着红绳,是张奶奶特意系的,说能辟邪。
陈露的素鱼雕到第十五条时,刀突然打滑,把鱼尾切歪了。“这可咋整?”
她举着歪尾巴鱼直跺脚,这是给老王家准备的,老王去年中风,说话不利索,可就盼着这条素鱼呢。“我有办法,”
李萌萌拿着红颜料跑过来,在歪尾巴上画了只小鲤鱼,“这样看着像鱼妈妈带着小鱼,更热闹。”
陈露看着画上的小鱼,突然笑了:“还是萌萌机灵,这鱼成了全家福。”
傍晚时,客人渐渐到齐了,素味斋的院里飘着卤味香、面香、还有冰糖莲子羹的甜香。张奶奶的孙子举着奥特曼,非要让奥特曼“吃”
福袋豆腐,陈露就用牙签插着个豆腐皮福袋,递到奥特曼手里,小家伙乐得直拍手。老周家的聋哑人老周,吃着荠菜饺子,给陈露比了个“好”
的手势,眼里的笑像灶膛里的火苗。
那桌“中西合璧”
的客人吃得格外欢,穿西装的年轻人举着素牛排拍照,说要朋友圈,配文“外婆第一次吃素牛排,说比真牛排健康”
。他母亲尝了口腊八蒜,辣得直吸气,却笑着说:“这味冲,像咱老家过年的辣白菜。”
王店长站在旁边看着,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原来不完美的菜,也能吃出团圆的味。
夜里十点多,客人渐渐散去,留下满院的空碗和笑声。邢成义收拾桌子时,现老李家的小屋漏了盏煤油灯,灯芯还在微微亮着,他走过去吹灭,闻到灯芯上沾着点莲子羹的甜香。陈露在灶房刷碗,听见巷口传来张奶奶的声音:“孙子说那豆腐皮福袋比油豆腐的好吃,明年还定!”
王店长坐在炉边,翻着那本记满了失误的账本:素鱼歪尾、素牛排淌汁、筷子不够、跳闸断电……可每处失误旁边,都被她画了个小笑脸。“成义,你看,”
她指着账本说,“咱这头一年的年夜饭,就像这歪尾巴鱼,不那么周正,可活泛着哩。”
邢成义往炉里添了块煤,火苗“噼啪”
跳起来,映得墙上的影子忽明忽暗。陈露端来刚煮的饺子,是用剩下的荠菜馅包的,有的皮破了,露出点绿,可咬一口,鲜得人直咂嘴。“明年咱得备足油豆腐,”
陈露咬着饺子说,“再多买十斤猴头菇,素牛排就得用真材实料。”
李萌萌趴在桌上,给画本最后一页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素味斋,院里的桌子有的歪着,有的缺腿,可每张桌上都亮着灯,像撒了满地的星星。她在画旁边写:“今年的年夜饭,菜有点歪,心却很圆。”
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落在素味斋的青瓦上,簌簌的响。灶房里的粥还温着,是给守岁的自己人准备的,粥里的莲子浮在面上,像颗颗圆滚滚的心愿。王店长看着窗外的雪,突然想起年轻时当家的说过,过日子就像熬粥,米多米少,火大火小,最后都能熬出暖乎乎的味。
素味斋的第一个年夜饭,就在这粥香和雪声里,慢慢酿成了往后日子里,最值得念叨的那段——不那么完美,却热热闹闹,像极了每个人家里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