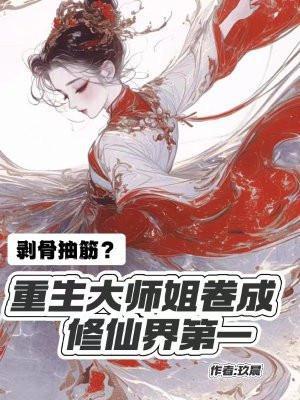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罗刹国鬼故事 > 第573章 瓦西里岛上的沉默(第2页)
第573章 瓦西里岛上的沉默(第2页)
鬼影大笑,笑声震得书架摇晃:“解放?看看你的手!你教学生历史,可你的儿子死在前线,你救不了他。知识救不了任何人,只制造孤独。”
它逼近,黑雾缠上伊万的脚踝:“选择吧,老头。要么闭嘴,像他们一样蠢;要么用他们的语言——把知识嚼碎,喂给他们当糊糊。否则,我吃掉你的舌头。”
伊万瘫坐在地,冷汗浸透衬衫。他想起亡妻临终的话:“伊万,有时沉默是最大的慈悲。”
第二天,他撕掉《秘闻录》的书页,烧成灰撒进涅瓦河。在厨房,谢尔盖抱怨面包配给少,伊万只点头:“是啊,真难。”
安娜哭诉儿子没来信,他拍拍她肩:“战争……总会结束的。”
邻居们惊讶,继而得意。谢尔盖拍他背:“早这样多好!知识?狗屁不如一勺猪油!”
市井的压迫松动了,伊万以为胜利了。但夜晚,鬼影再现,更庞大,嘴咧到天花板:“伪善!你的心还在说教。沉默不是投降,是背叛真理。用他们的语言,不是当哑巴,是把火种藏进灰里。”
它逼伊万誓:从此只说俗谚,只讲家长里短,把普希金换成“老天爷保佑”
。
伊万屈服了。他成了公寓的“新伊万”
。谢尔盖修收音机时,他不再提马可尼明,只说:“机器和女人一样,别太较真。”
安娜炖菜糊了,他附和:“糊涂点好,省得操心。”
邻居们接纳了他,甚至邀请他喝劣质伏特加。一个雪夜,大家挤在公共客厅听广播,播音员念着赫鲁晓夫的讲话。谢尔盖醉醺醺地喊:“领袖说集体农庄好,那就一定好!我祖父在乌拉尔种地,饿死时可没人管!”
众人哄笑。伊万心头一热,脱口而出:“谢尔盖,历史证明,强制集体化造成一九三二年大饥荒,乌克兰……”
话未完,灯光骤灭。黑暗中,鬼影暴涨,黑雾裹住整个房间。邻居们僵住,眼珠上翻,嘴角淌着白沫,齐声念诵:“闭嘴!闭嘴!闭嘴!”
鬼影的巨口咬向伊万:“你忘了誓言!知识是病毒,必须根除!”
伊万逃回房间,反锁门。书架轰然倒塌,书页如黑蝶飞舞,自动拼成字句:“最后机会:用他们的语言,或成为我们。”
他颤抖着写纸条:“谢尔盖,面包硬?试试泡在汤里,我奶奶的法子。”
塞进门缝。门外寂静。他以为安全了,却听见邻居们的脚步声聚集。门被撞开,谢尔盖带头,眼睛血红,手里攥着扳手;安娜举着洗衣棒;连瘸腿的米哈伊尔都拄着拐杖。他们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声音统一如合唱:“伊万·彼得罗维奇,你教我们知识……现在,我们教你沉默。”
扳手砸下时,伊万不躲。剧痛中,他看见鬼影融入邻居们的身体,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多头怪物。意识消散前,他听见鬼影的低语:“欢迎回家,新无言者。”
伊万没死,却消失了。他的房间被查封,书全烧了,灰烬撒在公寓院子里。邻居们生活如常,但多了一丝说不出的阴冷。谢尔盖不再偷零件,却总在夜半对着墙角喃喃自语;安娜的床单永远洗不干净,晾着时滴下黑水;米哈伊尔的收音机只播沙沙声,偶尔漏出伊万的声音:“一八一二年……”
最怪的是新住户——一个叫叶莲娜的年轻女教师。她搬进伊万的旧屋,试图组织读书会。第一晚,她刚说“同志们,让我们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灯就灭了。黑暗中,十六户人家的脚步声在走廊汇合,敲她的门,节奏整齐:“闭嘴……闭嘴……闭嘴……”
叶莲娜逃走了。从此,公寓再没人提书。厨房里,谢尔盖教孩子们唱新编的儿歌:“多说话的乌鸦,被雪埋掉;闭紧嘴的老鼠,吃到面包。”
安娜搓衣服时哼着:“知道太多?棺材钉牢。”
列宁格勒的冬天持续着。涅瓦河冻成铁板,寒风卷起雪沫,拍打着公寓的窗户。在瓦西里岛的这座灰楼里,知识成了最危险的传染病。而夜深人静时,如果你贴在门上听,会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混在邻居们的鼾声里,轻轻念诵普希金的诗句。但第二天问起,所有人都摇头:“没听见。你耳鸣了,同志。”
他们挤在公共厨房,分享一碗稀粥,蒸汽模糊了玻璃。窗外,雪地反射着月光,隐约映出十七个影子——十六个矮小佝偻,簇拥着一个高瘦的,正把手指按在嘴唇上,做着“嘘”
的手势。市井的压迫从未如此温暖,也从未如此冰冷。因为在这里,沉默不是金,是生锈的锁链,而锁链的另一端,拴着所有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