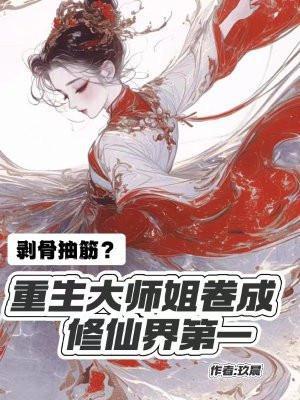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罗刹国鬼故事 > 第573章 瓦西里岛上的沉默(第1页)
第573章 瓦西里岛上的沉默(第1页)
一九五三年的初冬,列宁格勒的寒风像一群被放逐的幽灵,在涅瓦河畔的街巷间游荡。霜雪覆盖的屋顶如同冻僵的巨兽脊背,压得整座城市喘不过气。在瓦西里岛上,一座灰扑扑的五层公寓楼蜷缩在街角,它的砖墙斑驳,窗户糊着旧报纸,每扇窗后都透出昏黄的灯光,像垂死人的眼睛。这座楼建于沙皇时代,如今是典型的苏联集体公寓——一个由十六户人家共享的笼子。走廊狭窄得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战场,水龙头滴答作响,如同时间的丧钟。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卷心菜汤、劣质烟草和潮湿羊毛的混合气味,那是市井生活最赤裸的压迫:你无法呼吸,却必须活下去。
住在这里的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是个六十七岁的退休历史教师。他瘦高个子,背微驼,鼻梁上架着一副磨花的圆眼镜,镜片后藏着一双总在思索的眼睛。伊万的房间在三楼尽头,不足十平方米,却塞满了书: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书堆在椅子上、床上,甚至窗台上。这些书是他的堡垒,也是他的牢笼。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教了三十年俄国史,能背诵普希金的每一行诗,细数基辅罗斯的每一场战役,甚至知道十二世纪诺夫哥罗德商队的关税细节。但革命和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只留下这些泛黄的纸页。邻居们叫他“教授”
,语气里混着敬畏与不屑。在集体公寓的日常里,知识是种奢侈,而奢侈招人嫉恨。
伊万初来时,曾天真地想点亮这黑暗的角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在基洛夫工厂干了二十年车床的壮汉,常在公共厨房抱怨配给面包太硬。伊万会放下茶杯,温和地说:“谢尔盖兄弟,这让我想起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撤退时,俄国农民用黑麦面包当武器的故事……”
谢尔盖却粗暴地打断:“闭嘴,老学究!面包就是面包,历史填不饱肚子。”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守寡的清洁工,为儿子参军的事哭泣时,伊万引用托尔斯泰安慰她:“安娜,战争是历史的脓疮,但人性的光辉……”
安娜却抹着眼泪啐道:“你懂什么?你儿子活着,我儿子在斯大林格勒烂泥里!”
伊万的善意像雪球滚进火炉,瞬间蒸。渐渐,邻居们学会了绕着他走。走廊里,他脚步声响起时,门会“砰”
地关上;厨房排队打水,人们突然记起忘了关煤气。市井的压迫不是刀剑,是无声的冰水,一滴一滴,冻僵你的灵魂。
那年十一月,列宁格勒的雪下得格外早。伊万在旧货市场淘到一本破旧的书,封面烫金字母已剥落,只余下模糊的纹路。摊主是个独眼老头,裹着肮脏的毡靴,他神秘兮兮地说:“这书来自普斯科夫的修道院,只卖给你,伊万·彼得罗维奇——它认得读书人。”
伊万付了三卢布,书轻得像片枯叶。回家后,他拂去灰尘,露出标题:《东斯拉夫民间秘闻录》。书页脆黄,插图是扭曲的森林精怪和长着人眼的月亮。他本以为是民俗学资料,但第一行字就攫住了他:“知识是火,火能暖人,也能焚屋。智者慎言,愚者自缚。”
伊万笑了,这不过是迷信。他连夜研读,现书中记载着许多失传的谚语和仪式,比如如何用桦树枝驱邪,或在冬至夜对月亮低语愿望。他决定试一试——不是为迷信,而是为融入。邻居们信这些,他想,用他们的语言,或许能重建桥梁。
第二天傍晚,伊万在公共厨房熬着稀粥。谢尔盖正骂骂咧咧地修水龙头,安娜在搓洗衣服。伊万清清嗓子:“朋友们,今天是谢肉节前夜,按普斯科夫的老传统,我们该把第一勺粥洒在地上,敬土地神,保佑来年丰收。”
他舀起一勺,郑重地倒在油腻的地板上。谢尔盖猛地抬头,脸涨得猪肝色:“你疯了?粮食是国家的,糟蹋它犯法!土地神?呸!那是沙皇的毒药!”
安娜也缩回手,肥皂水滴在围裙上:“伊万·彼得罗维奇,教堂都关了,你还搞这些黑魔法?”
伊万耐心解释:“这不是魔法,是文化遗产……”
话未说完,谢尔盖一拳砸在水槽上,锈水溅了伊万一身:“闭上你的嘴!我们工人用双手建设社会主义,不靠鬼神!”
人群聚拢,眼神像刀子。伊万退回房间,心沉甸甸的。书页在灯下泛着幽光,他翻到一页:“当众人拒斥真理,愚昧的幽灵将苏醒。”
他以为是隐喻,没在意。
怪事始于第三夜。伊万被一阵刮擦声惊醒,像老鼠在啃墙,却更尖利。他点燃油灯,现书架上的《战争与和平》散落在地,书页撕得粉碎。窗玻璃结满冰花,竟映出模糊的鬼脸——歪嘴斜眼,舌头耷拉到下巴。他揉揉眼,鬼脸消失了。次日早餐时,安娜尖叫着冲进走廊:她晾在厨房的床单全被染成血红色,水槽里漂浮着死乌鸦。谢尔盖的扳手不翼而飞,却在他枕下找到,沾满黑泥。恐慌像霉菌蔓延。邻居们开会,集体公寓的“委员会”
——由谢尔盖、安娜和退休钳工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组成——指控伊万:“是你搞的鬼!那本邪书招来了灾祸!”
伊万辩解:“科学能解释一切,也许是管道漏气……”
谢尔盖吼道:“又是你的科学!昨天洒粥,今天死鸟,明天是不是要挖我们祖坟?”
米哈伊尔,这个平日沉默的老头,突然颤巍巍地说:“我祖父在斯摩棱斯克见过这种事……是‘无言者’回来了。”
众人倒吸冷气。“无言者”
是东斯拉夫传说:一个因多嘴被全村活埋的智者,死后化作幽灵,惩罚所有炫耀知识的人。伊万想反驳,但安娜的眼泪和谢尔盖的拳头让他闭嘴。他回到房间,书自动翻到一页,墨字浮现:“他们不需要真理,只需安宁。要么沉默,要么用他们的话。”
第四夜,寒流刺骨。伊万裹着毯子读书,油灯忽明忽暗。书页上字迹蠕动,聚成一行:“你听见市井的低语了吗?”
他侧耳,走廊传来窃窃私语,不是人声,是无数细碎的摩擦,像虫群爬行。门缝下渗进黑雾,凝成一个矮小人影——它没有脸,只有一张巨大的嘴,嘴角咧到耳根,牙齿是碎玻璃片。它飘近,声音如生锈的门轴:“伊万·彼得罗维奇……你懂太多,却不懂人。”
伊万颤抖:“你……你是谁?”
鬼影的嘴开合:“我是这栋楼的呼吸,是十六户人家的恐惧和无知。他们怕你的知识,像怕冬天的狼。你纠正他们的错,却不知错是他们的铠甲。”
它指向窗外:雪地里,邻居们的剪影在跳舞,动作僵硬如木偶,嘴里哼着走调的《国际歌》,眼睛空洞。鬼影继续:“谢尔盖在工厂偷零件换伏特加,安娜藏了黑市黄油,米哈伊尔的儿子逃兵役……你的真理会撕碎他们的安宁。他们宁愿活在谎言里,因为谎言暖和。”
伊万争辩:“但真相能解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