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去小说网>穿书就卖男主?哥哥你听我狡辩 > 第201章(第1页)
第201章(第1页)
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忽然低笑一声,“怕疼?小时候被马蜂蛰了手,哭着喊着要把蜂巢捅了的劲儿呢?”
“那能一样吗?”
谢檀溪嘴硬,视线却瞟向别处,不敢看他近在咫尺的脸。
记忆里他们总是摔伤,各种各样的伤,那时谢斯屿上药的手总是很轻。
他会先把伤药倒在掌心搓热,再小心翼翼地覆上去,指腹碾过伤口边缘时,力道轻得像怕碰碎琉璃。
若是她疼得抽气,他就会停下来,从怀里摸出颗糖塞进她嘴里,声音是少年人独有的清润。
“忍一忍,好了带你去外面,听别人说外面的人很好,不像谢风那么吓人,也不会打人。”
那时他总是带着少年气,混着伤药难闻的味道,成了她童年里最安心的味道。
有次她胳膊被试管玻璃碴子划得深,他蹲在她面前,垂着眼睫一点点清理伤口里的玻璃碴子。
谢斯屿长长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浅浅的阴影,那时还是个最好的哥哥。
可如今再看他的手,骨节分明,指腹覆着层薄茧,动作利落得近乎果决。
方才喷药时,他甚至没给她躲闪的机会,指尖按在伤口上的力道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再没有半分当年的温吞。
迟到的传来尖锐的刺痛,像是有细针在皮肉里钻。
谢檀溪闷哼一声,指尖攥紧了他的衣袖,她明白谢斯屿动作迅速上药是为她好。
等那阵疼劲过去,伤口竟真的不流血了,只余下微凉的麻木感。
“这是什么好东西?”
她惊讶地看着伤口上淡淡的油膜。
“不止谢风会做实验。”
谢斯屿收回手,将喷雾揣回袖中,动作自然得仿佛做过千百遍,“别碰,明早就能好。”
他转身要走,却被谢檀溪拉住了衣角。
“你的伤……”
“没事。”
他头也不回,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哑,“我比你耐疼。”
可谢檀溪分明看见,他转身的瞬间,指尖在身侧蜷了蜷,指节泛白。
“不疼也要治,我可不想你倒在半路。”
谢檀溪强硬拽住他的衣服尾巴。
谢斯屿被拽得一个趔趄,后背的伤口被牵扯得发疼,他皱眉想挣开,“没事,就一点伤,不疼。”
“不疼?”
谢檀溪手劲大得惊人,指尖攥着他衣襟的力道带着不容置疑的执拗,“后背的血都浸到外套了,是又想故技重施,让我心疼你?”
话音未落,她已经用力扯开了他外套。
衬衫也被带着滑落肩头,露出里面渗着暗红的血,后腰处的布料早已被血浸透,晕开大片暗沉的痕迹。
谢檀溪神色一暗,这男主光环什么时候减弱了?
流那么多血,真的不会有事?
谢檀溪控制不住用手碰了碰他青紫的后背,“不痛才有鬼。”
谢斯屿的呼吸顿了顿,显然没料到她会如此直接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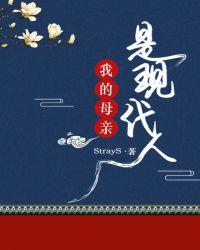
![(综英美同人)[综英美]我和我的逆转系统+番外](/img/16862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