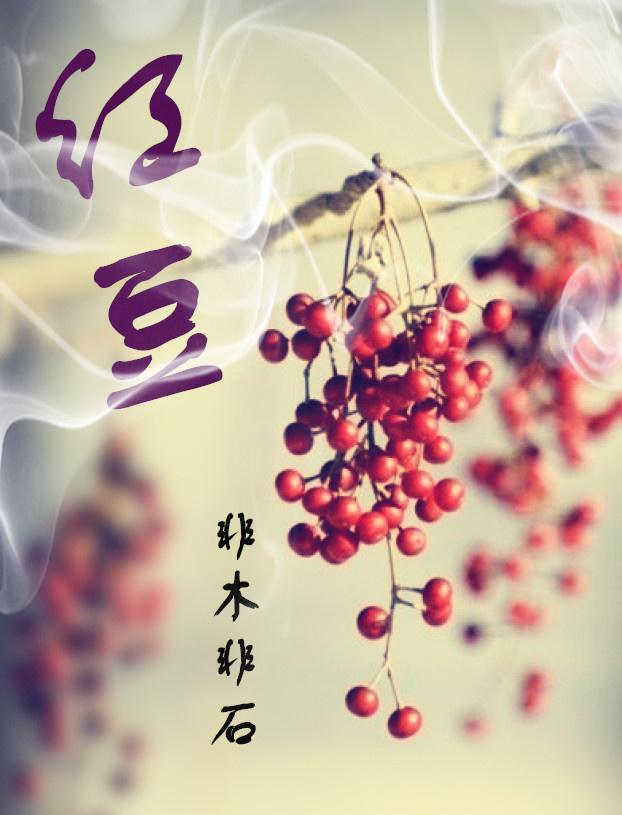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天幕:从带老朱看南京大屠杀开始 > 第414章 二十四孝的含金量(第2页)
第414章 二十四孝的含金量(第2页)
刘彻微微颔:“卫霍二卿之论,甚合朕意。孝为百行之先,然需以智勇为辅,且不能悖于公义大局。韩炳故事,可作民间谈资,显孝道之力量。然于国家选士、治军理政,则须重纪律、讲谋略、顾全局。朕令郡国举孝廉,非仅取能冒死救亲者,更取其德行足以化民、才具足以任事之人。至于‘盗匪四起’,根源在于朝政失修、武备不彰。北宋末年景象,足为镜鉴。传谕地方长吏:平时当勤修武备,严治盗贼,勿使百姓陷于需自决生死以全孝道之境地。若有如韩炳般事迹,可酌情旌表其孝,然必须申明,守土安民乃官府之责,非百姓之常役。”
**唐,贞观年间,太极殿。**
李世民与群臣观天幕,皆露感慨之色。李世民道:“乱世孝子,其行可风。然其间分寸得失,亦值思量。诸卿且议。”
房玄龄道:“陛下,此事可析数层。其一,孝道之践行。韩炳闻母危,不避险阻,毅然赴救,此孝心之纯粹,行动之果决,足令闻者动容。‘仁者之勇’,此评恰当。其二,危局之处置。其行为本身风险极高,既可能危及自身,亦可能影响城防。幸得贼人退避,母子俱安,成就佳话。然不可视为处险之范式。其三,贼人反应。‘群贼避退’,此语耐人寻味。或贼本乌合,见其气势而怯;或贼中亦有天良未泯者,为其孝行所感;亦可能是贼众误判,以为其后有援。此事凸显个人精神力量于特定情境下之作用,然非普遍规律。其四,史笔褒扬。墓志铭特书此事,意在彰孝励俗,尤其于朝代更迭、金统治下,强调此类汉人士大夫之儒家德行,或有深意。”
魏征肃然道:“陛下,臣以为此事之核心,在于‘私德’与‘公义’之潜在冲突。韩炳所为,是尽人子之私德,然其身为城中一分子,于城围之际擅出,客观上可能损害守城之公义。所幸未酿恶果。此事提醒为政者,教化百姓,于倡扬孝悌等私德时,亦需强调公民之责、公共之利。使民知,在太平之时,孝养父母;在危难之际,除保全亲人外,亦当尽力维护乡梓、协助官府。韩炳若能在出城前通报守将,或能稍减其行为对公义之潜在损害。然其情急之下,恐难周至。故评价此事,当怀悲悯,亦需明理。”
李靖从军事角度言:“陛下,单就行动而言,韩炳可谓胆大心细(或云心粗)。其选择缒城而非闯门,是避贼正面;仅带二三仆从,轻装疾行,是求;持木梃而非利刃,或为顺手取用,亦显其救母心切,非为搏杀。贼众退避,可能是被其突如其来的行动和决绝气势所慑,一时未能反应。此等个人突击行为,于大军对阵中几无价值,然于小规模混乱中,或能收奇效。然为将者,断不可鼓励士卒效仿。军纪如山,统一行动方是制胜之本。此故事于民间传颂可也,于行伍之中,当强调服从号令、协同作战。”
李世民颔:“诸卿剖析入微,情理兼备。韩炳孝勇,诚可嘉尚,尤在末世乱离之秋,更显人性光辉。然其行不可盲目效法,尤不可因褒扬此类极端个例,而轻忽了朝廷保境安民之根本责任。朕常思,使天下百姓皆能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少有所怀,无需履此等险境,方为至治。至于墓志铭之书写,自有其时代与个人之考量。传旨礼部、国子监:编纂劝孝教本,可收录此类故事,然需附加按语,阐明孝道之贵,在于平日之奉养、危时之关切,更在于促使朝廷社稷安宁,使天下父母皆免于颠沛流离之祸。勿使学子误以为,惟独行冒险方为至孝。”
**宋,太祖朝,崇政殿。**
赵匡胤观天幕,面色沉凝。宣和末年,那是他赵宋天下未来将致的惨淡图景?盗匪围城,百姓需自缒城救亲……他心中涌起一股寒意与怒气。
赵普见皇帝神色,知其所虑,沉声道:“陛下,天幕所示,乃百余年後末世景象。然其肇因,必积于平日。‘盗匪四起’,根在政令不行、赋役不均、武备废弛,官吏或贪墨或庸懦,不能抚民御盗。至使贼势猖獗,围困州县,百姓骨肉离散,需以身犯险,此朝廷之耻也!韩炳孝行固然可彰,然其背后,是无数家庭之血泪与朝廷统治之失败。我朝立国未久,正当以此为鉴,整饬吏治,强固边防,肃清内盗,务使天下晏然,不复有此等惨事。”
石守信道:“陛下,末将看了恼火!盗匪都能围城了,当地的官兵是干什么吃的?让老百姓自己拿棍子去救人?这韩炳是条汉子,但这事不该生!咱们禁军、厢军,就得把地方守好了,让贼人不敢靠近城池!那些州县官,守土有责,城防怎么布的?能让贼人围上来?该查办!”
王审琦道:“韩炳后仕金朝……此亦可见当时士人之无奈与选择。然其救母之事,在金人统治下之墓志中犹得褒扬,可见孝道纵在异代,仍被视为重要德行。我朝以仁孝治天下,对此等孝行,自当旌表。然更重要的,是杜绝产生此类孝行的悲惨环境。须使‘盗匪四起’永不重现于大宋疆土。”
赵匡胤重重吐出一口气,斩钉截铁道:“你们说得对!这故事,让咱看到的是咱大宋未来可能的疮疤!咱绝不能让它生!赵普,你们中书门下,立即拟旨:严令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知县,限期清查辖境,缉捕盗贼,整修城防,储备粮械。凡有盗匪生不能及时扑灭,乃至滋扰城池者,地方官一律严惩不贷!另,着枢密院议定更戍法细则,加强地方驻军训练与巡视。至于韩炳此类事迹……可令地方访查,若属实,予以旌表,立碑或免其家徭役,以励风化。但天下告示必须申明:朝廷力保百姓安宁,此类冒险救亲之事,朕不希望再听到!”
**宋,徽宗宣和年间(当代),东京汴梁。**
赵佶(宋徽宗)本人或许正与蔡京、童贯等臣子观天幕,如坐针毡。天幕直言“宣和末年,盗匪四起”
,且举出山东千乘被围之例,这不啻于一道惊雷,劈在繁华的东京梦华之上!预言般的警示,让这位沉溺于书画、艮岳的皇帝,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
朝堂之上一片死寂。蔡京等权臣面色灰败。他们深知,如今河北、山东等地,确有宋江、方腊等变乱(时间略有参差,或泛指盗匪),但多被掩盖或轻描淡写。如今天幕将未来(或正在生)的乱象赤裸裸展现于万朝之前,更是将地方治理的溃败、盗匪的猖獗公之于世,令朝廷颜面扫地。
有耿直之臣或许趁机出列,痛陈时弊:“陛下!天幕示警,言犹在耳!今山东、河北、两浙,盗贼实已滋蔓,州县不能制。若不及早措置,整军经武,选派良吏,减轻民负,则‘盗匪围城’之祸,恐不止于千乘!韩炳一人之孝,难掩天下万千离散之悲。乞陛下罢花石纲,停不急之役,黜退奸佞,任用忠良,专意安内,则社稷幸甚!”
赵佶惶惑无措,看向蔡京。蔡京强自镇定,或辩称:“陛下勿忧,天幕所言,或是后世夸大。今虽有毛贼,然王师所向,指日可平。韩炳之事,正显我朝民风淳厚,孝义感人。当务之急,是严禁民间妄传此幕,以免蛊惑人心。”
然其言辞已然苍白。
天幕的显现,无疑给已然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政局,投下了一颗巨大的石子,激起的波澜难以预料。是促使朝廷改弦更张,还是加其崩溃,抑或仅仅成为一段插曲,皆在未定之天。
**明,洪武朝,南京奉天殿。**

![我不是在动物园吗?[星际]](/img/32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