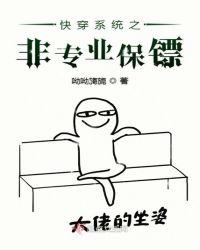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天幕:从带老朱看南京大屠杀开始 > 第386章 先帝想的人是真不少(第4页)
第386章 先帝想的人是真不少(第4页)
朱标低声道:“儿臣只觉得……心寒。为国建功的臣子,死后家属竟连申冤哭泣,都要被如此‘理直气壮’地压制。为君者至此,何其薄凉。”
**——**
光幕画面再次变化。
这一次,地点似乎是在宫帐内,气氛更加凝重。述律平面前,站着一位身着汉家衣冠的男子,年约四旬,面容儒雅,但此刻脸色惨白,身体微微抖。周围是眼神凶狠的契丹武士,以及一些面带兔死狐悲或幸灾乐祸之色的契丹贵臣。此人乃降臣,姓赵,汉官出身,颇受耶律阿保机生前赏识。
述律平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赵先生,先帝生前亦看重于你。如今先帝寂寞,需要忠诚之人陪伴。你对先帝,忠诚否?”
熟悉的问话,熟悉的杀机。
帐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赵姓降臣身上。那些契丹贵臣有的冷漠,有的闪过一丝同情,但无人出声。谁都明白,这是皇后要继续清洗,甚至可能意在试探或牵连更多人。
赵姓降臣的冷汗浸湿了内衣。他知道,回答“忠诚”
,立刻就会像帐外那些同僚一样,被拖出去砍头;回答“不忠”
,更是死路一条,且累及家人。绝境之下,求生的本能和某种被逼到极处的愤怒,催生出了一股急智,或者说,是孤注一掷的反击。
他忽然抬起头,不再是畏惧颤抖的模样,反而挺直了脊背,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悲愤与讥诮的神情,声音清晰,甚至有些响亮地反问道:“皇后娘娘!微臣等身为男子,于地下陪伴先帝,固然是尽忠。然而,若论与先帝最亲近、最受先帝信赖思念之人,难道不是皇后娘娘您吗?”
此言一出,满帐皆惊!连那些契丹武士握刀的手都抖了一下。
述律平显然没料到对方会如此反问,猛地一怔,苍白的脸上瞬间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惊愕、被冒犯的怒意,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刺痛。她是耶律阿保机的结妻子,并肩创业的原配,感情自然非比寻常。
赵姓降臣见她没有立刻作,胆子似乎大了一些,或者说,他已知必死,索性豁出去了,继续大声道:“先帝若真觉地下寂寞,最希望陪伴在侧的,必然是皇后娘娘您啊!娘娘与先帝夫妻一体,情深义重,无人能及!臣等这些外臣,纵有忠心,又岂能替代娘娘分毫?”
帐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述律平。这番话,简直是将了皇后一军!你不是要人“尽忠”
陪先帝吗?最该去陪的,不就是你自己吗?
述律平沉默了。她的胸膛微微起伏,眼神剧烈闪烁,握着座椅扶手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白。愤怒、难堪、悲伤,还有一丝被戳中心事的狼狈,在她心中翻腾。她能说什么?说自己不想死?那之前所有“尽忠”
的说辞都成了笑话,再也无法以此杀人。说自己愿意去?那更是荒谬。
时间一点点流逝,压力仿佛实质般凝聚在帐中。就在所有人以为述律平会暴怒,立刻下令将此人碎尸万段时,她忽然哭了。
这一次的哭声,与之前不同。少了表演的成分,多了真切的痛苦与挣扎。她泪如雨下,看着那赵姓降臣,又仿佛透过他,看着虚空中的某处。
“赵先生……你好利的词锋。”
她哽咽着,声音破碎,“我难道不想去陪伴先帝吗?我日夜思念,痛不欲生!恨不能立刻随他而去!”
她抬起自己戴着玉镯的右手,纤细,但绝不柔弱,那是一双曾挽弓射箭、也能执笔批文的手。
“可是……”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决绝,“大辽初立,国基未稳,皇子年幼!先帝将江山托付于我,我岂能因一己私情,弃国家于不顾,弃幼子于险地?”
她猛地将右手伸到面前,眼中闪过一丝疯狂而痛苦的光芒:“我对先帝之心,天地可鉴!若非要为了这大辽江山,为了我们的骨血,我必即刻追随先帝于九泉!今日,既然不能全身相殉,就让我的这只手——这只曾与先帝携手定江山的手——先去陪伴先帝,以表我忠贞不渝之心!待他日幼主长成,江山稳固,我必亲赴黄泉,向先帝请罪!”
话音未落,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述律平左手不知从何处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刃,毫不犹豫地朝着自己伸出的右手手腕,狠狠剁下!
“噗嗤!”
利刃切入骨肉的声音令人牙酸。血光迸现!
一只戴着玉镯、保养得宜的纤手,齐腕而断,掉落在铺着毛毯的地面上,手指甚至还微微抽搐了一下。猩红的鲜血如同泉涌,从断腕处喷溅而出,瞬间染红了述律平的素白衣袖和前襟。
“皇后!”
帐内众人魂飞魄散,惊呼声炸响。离得近的侍女尖叫一声,几乎晕厥。契丹武士也惊呆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
述律平身体晃了晃,脸色惨白如鬼,额头上瞬间布满豆大的冷汗。剧烈的疼痛让她几乎站立不稳,但她死死咬住下唇,没有出痛呼,只是用左手死死按住右臂断腕上方,试图止血。她的眼神,依旧死死盯着地上那只断手,又缓缓移到面无人色、已然吓傻的赵姓降臣脸上。
“现在……”
她吸着冷气,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血腥味,“你,还有何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