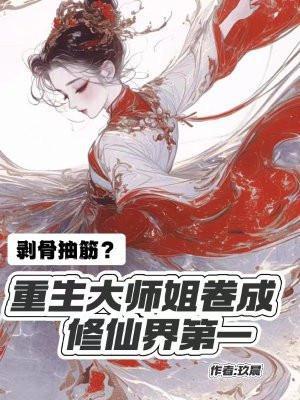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离婚后我走向幸福人生 > 第11章 上帝(第1页)
第11章 上帝(第1页)
林秀兰洗完碗,把手擦干,摘下围裙,慢慢走到客厅。
她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站在窗边,望着外面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影。
秋日的阳光薄而冷,照在她脸上,却照不进她心底那片翻腾的暗潮。
她忽然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本书——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那时她只是随便翻翻,觉得那些句子狂野又晦涩,像雷霆砸在玻璃上。
可现在,那些句子像被时间重新点燃,一句一句在她脑子里回响。
“上帝已死。”
她低声自语,唇角微微牵动。
如果上帝真的死了,那道德的枷锁呢?那套用血缘、用“母亲”
“儿子”
这些标签铸成的铁链呢?它还剩下什么力量?
她转过身,背靠窗台,双手抱胸,像在和自己辩论。
从叔本华的角度看,人生就是意志的盲目冲动。
欲望是本体,理性只是表象的奴隶。
她和李然的结合,不正是那股原始的、不可抑制的生命意志在爆吗?
血缘的禁忌,不过是社会为了自我保存而编造的幻影。
剥掉这层幻影,剩下的只是两个肉体、两股意志,在最赤裸的层面相互吞噬、相互肯定。
她闭上眼,脑海里浮现昨晚的画面儿子埋在她身体里,一次次顶到最深处,像要把她撕裂,又像要把她填满。
那一刻,她感受到的不是罪恶,而是某种极致的“肯定”
——对生命的肯定,对欲望的肯定,对自己作为女人的肯定。
尼采会怎么说?
“你要成为你自己。”
永恒轮回的考验如果这一生必须无限重复,你是否愿意再次拥抱这一切?
她问自己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她还能再活一次,她会不会再次在儿子睡着时偷闻他的内裤?
会不会再次用他的小手拳交自己?
会不会再次在教室里跪下来含住他的肉棒,把他的精液咽下去?
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不止一次。
她愿意重复一千次、一万次。
因为那不是堕落,而是她最真实的自我在绽放。
乱伦的标签,不过是弱者用来安慰自己的道德鸦片。
强者——或者说,真正敢于直面生命的人——会撕碎这张标签,把它踩在脚下,然后赤裸裸地拥抱那股吞噬一切的激情。
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萨特会说人是被抛入世界的,注定要自由选择自己的本质。
她选择了成为亲生儿子的女人、儿子的婊子、儿子的精液容器。
这不是被强迫的,不是被本能驱使的被动结果,而是她主动的、清醒的、残酷的自我创造。
她在那一刻,对自己说“是的,这就是我。我不后悔。我不求宽恕。我就是这样。”
甚至,她可以再往前推一步,用福柯的权力观点来看乱伦禁忌本身就是权力话语的产物,是社会为了控制身体、控制繁衍、控制家族而设下的规训装置。
她和李然的结合,是对这种装置最彻底的反叛——不是偷偷摸摸的反叛,而是光明正大地、用身体去践踏、去嘲笑、去瓦解它。
她忽然轻笑出声,声音很低,却带着一种解脱的快意。
“然然……妈不是疯了。妈只是……终于活得像个人了。”
林秀兰从窗边走开,脚步轻得像踩在云上。
她没有回主卧,而是拐进了李然的房间——那间十九平米的小屋,床单还是她昨晚亲手换的,带着阳光和淡淡的洗衣粉味。
现在,房间里却残留着另一股气味儿子的体香,混合成一种只有她自己能分辨的、属于“禁忌”
的独特香气。
她关上门,反锁。动作很慢,像在给自己时间酝酿。
然后她站在床边,低头看着那张单人床。
床头柜上放着李然昨晚随手扔的T恤,她伸手拿起来,贴在脸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棉质布料上残留着他的体温、他的汗、他的男性荷尔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