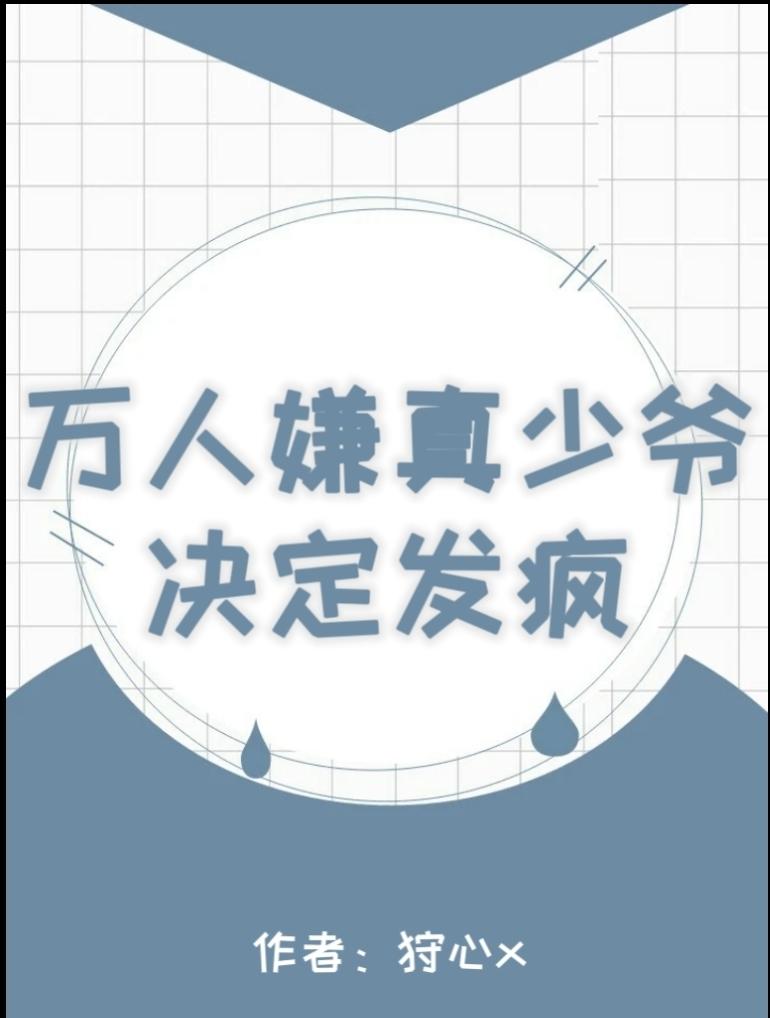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爱无理 > 第8章 下周回去陪你(第2页)
第8章 下周回去陪你(第2页)
“他还是出轨了。”
初母低声说了一句,给这段关系下了最终的判词。
“男人,都那样。”
初母的声音很轻,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眼角溢出一滴泪,随后便是长久而克制的啜泣,她低着头,肩膀微微起伏。
初初没有说话,只是把杯子往母亲那边推了推,又替她倒了点温水。
“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初母抬手抹了把眼泪,笑得有些勉强,“那几年,他回家的时候,眼睛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了。”
“人心就是说变就变的,以前在一起的打拼的日子,他都不认了。”
一时间,包间里很安静,只有空调低低的运转声。窗外的霓虹映进来,落在桌面上,一块一块,像被切碎的时间。
“妈。”
初母抬头看她,眼睛有些红,却已经平静下来。
“你别学我。”
她忽然说,“也别学你爸。”
初初麻木地点头。
她想起两年前心理医生的诊断原生家庭的创伤让她成为了“空心人”
。
她从父母的残局中学到,爱是这世上最荒诞的赌博,只要不入场,就永远不会输。
她并非没有尝试过自救。
高三那年遇见杭见,那是她荒芜生命里第一次出现的异数。
杭见曾用那种不顾一切的、滚烫的爱,几乎要缝补好她破碎的认知。
在那段日子里,她曾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幸运的,以为她可以挣脱原生家庭的诅咒,和她的父母不一样。
可生活最擅长在人最笃定的时候给予重击。
大二那年,那个曾许诺要给她一个“家”
的杭见,以一种最讽刺的方式——出轨,彻底杀死了那个试图自愈的初初。
那一刻,她不仅失去了杭见,更失去了对“爱”
这个字最后的一丝信念。
原来没有例外,宿命早已在多年前那个落满蜂蜜的玄关处埋好了伏笔。
这种加倍的痛苦像是一场盛大的献祭,耗尽了她身体里最后一丝生机。
她终于不再挣扎,在废墟上彻底坐了下来,任由自己退化成一个心如止水的“空心人”
。
她现,只要不相信爱,甚至只要不去爱,就不会有伤害,没有麻烦,也就没有痛苦。
爱无能。
把母亲送回家安顿好后,她独自坐在屋外的台阶上,初夏的风一阵阵吹过她梢,手肘抵着膝盖,点燃了一根薄荷款七星,烟头的星火在黑夜里时闪时暗,听着蝉鸣,她开始呆。
叮叮叮——
手机不断震动,一通电话,一个好友请求。
电话是游问一的。
好友请求是乔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