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去小说网>港综:洪兴四九仔,踩靓坤扎职 > 第974章 七叔的葬礼仪式(第2页)
第974章 七叔的葬礼仪式(第2页)
周晟鹏站在b-7区外廊阴影里,指尖抚过一根细如丝的钢琴钢丝。
它横贯于两根锈蚀立柱之间,距地仅四十厘米,涂了哑光黑漆,浸过海水,冰凉,无声,锋利得能切开牛皮。
第一个枪手低头跃过舱门门槛,脚踝刚触钢丝——
“嗤。”
没有惨叫,只有皮肉被高切割的闷响,接着是膝盖以下突然失去支撑的失衡扑倒。
第二人反应极快,翻身举枪,枪口尚未抬起,脚踝已被另一道斜向钢丝掠过。
他仰面栽倒,喉咙里涌出嗬嗬声,双手徒劳抓挠着自己齐齐断开的双脚。
周晟鹏没看他们。
他转身,右手已按在腕表遥控界面上——那个从王怀德中山装内袋顺走的、表面刻着“haIkuI-o7”
的黑色方块。
拇指悬停,呼吸未乱,心跳平稳如秒针。
三秒后,他按下。
远处海面,那艘被遗弃的银灰快艇猛然加,引擎啸叫撕裂夜空,船高高扬起,以近乎自杀的角度,直刺七叔旗舰右舷油舱侧翼——那里,焊接补丁下,一道三年前未报备的应力裂痕正随航微微翕张。
快艇撞上的前一瞬,周晟鹏已纵身跃向舷边滑索支架。
钢索绷紧如弓弦,他坠入浓雾,身影被镁粉烟幕吞没的刹那,左手探入胸前内衬,指尖触到那枚Zp-o1钛合金芯片——它正微微烫,仿佛在回应某种遥远的、即将苏醒的频率。
滑索尽头,减压舱顶部冰冷的弧形钢壳在雾中浮现。
他单膝落地,靴底碾碎一层薄霜。
舱内,郑其安正将周宇平置在狭窄担架上,听见动静猛地抬头,只见周晟鹏抬手,指向舱壁一处锈蚀的方形检修盖板——盖板背面,隐约可见半截裸露的广播线路接口。
周晟鹏没说话。
只是从怀中取出一枚火柴盒大小的便携音频模块,插进接口,轻轻一按。
模块指示灯亮起幽绿微光。
舱内死寂。
唯有远处,快艇撞入油舱的巨响尚未抵达耳膜,而那一声沉闷、嘶哑、混着火焰噼啪声的男声,已在锈船所有残存扬声器里,悄然启动倒计时:
“……三。”
“二。”
“一。”
爆炸的冲击波尚未抵达耳膜,声音却已先一步撕裂——不是轰然巨响,而是低频共振:整艘锈船如垂死鲸骨般猛然一弓,龙骨在千吨水压与烈焰反冲中出濒断的呻吟。
甲板掀飞、舱壁内凹、镁雾被气浪狠狠犁开一道斜向裂口,惨白光柱骤然刺入,映出周晟鹏单膝跪在减压舱顶的剪影——他肩头军用防弹衬垫已被灼出焦痕,左耳缘渗血,却未抬手去擦。
他听见了。
不是火,不是金属扭曲,而是声音——那声音从锈船残存的十二个扬声器里同时涌出,嘶哑、破碎、带着肺叶烧穿后的漏气杂音,混着1994年老式磁带机特有的沙沙底噪:
“……我烧的不是祠堂……是账本……是你们递到我手里的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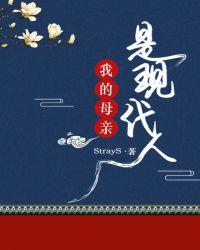
![(综英美同人)[综英美]我和我的逆转系统+番外](/img/16862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