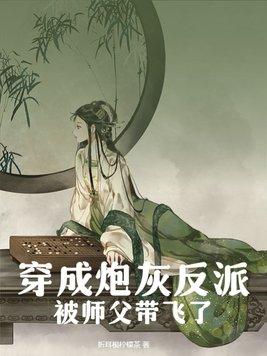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七十一章 做梦梦到未来(第3页)
第一百七十一章 做梦梦到未来(第3页)
徐涛忽然站起来,往菜园的方向望——其实现在那里还只是片空地,但他仿佛已经看见薄荷在风里摇晃,玫瑰爬满竹架,邢师傅的土灶冒着烟,熊立雄蹲在菜畦里给黄瓜搭架,陈露举着玻璃罐在摘桂花,罐口沾着金闪闪的花瓣。
“我还想在菜园中间挖个小池塘,”
他抱着吉他往前走了两步,像是在丈量池塘的大小,“里面养几尾鱼,种些荷花。客人坐在池边的石头上听我弹琴,鱼从水里跳起来,溅起的水珠落在琴弦上,说不定能弹出新调子。到时候写《素味斋的夏天》,里面有蝉鸣,有荷香,有邢师傅喊‘开饭了’的声音。”
王店长笑着摇头:“你们这想法啊,能从中秋说到明年清明。不过叶总说了,菜园子旁边可以盖几间小屋,给来帮忙的客人住。比如金姑娘明年再来,要是想多待几天,就住小屋里,早上跟着陈露摘桂花,中午帮邢师傅择菜,晚上坐在院子里教咱们唱她国家的歌谣,多好。”
“那小屋得铺木地板,”
陈露说,“墙上挂着客人留下的照片——有外国小伙学包素包的样子,有张奶奶的孙子举着石榴糕的笑脸,还有咱们在天台看月亮的合影。屋顶上得装个天窗,晚上躺在床上,能看见月亮从桂花树后面爬上来,像小时候外婆家的老屋。”
熊立雄已经开始盘算小屋的家具了:“我要做张木桌子,就用后院那棵枯死的老枣木,锯成板,打磨得光溜溜的。客人可以在上面写留言,今天谁吃了邢师傅的红烧肉(哦不对,咱们是素菜馆,那就写‘吃了邢师傅的素烧萝卜’),明天谁听了徐涛的新歌,多少年以后,桌子上刻满了字,像本厚厚的日记。”
邢成义把晾温的银耳汤端给张奶奶家,回来时手里攥着颗糖,说是小家伙塞给他的。“张奶奶说,等她孙子再大点,就让他来学做素包,”
他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甜丝丝的味道漫开来,“还说要把她的老面引子传给孩子,说‘素味斋的面得用老面,才够劲道,就像过日子,得有老根牵着,才稳当’。”
王店长听见这话,忽然从柜台上拿起个小布包,解开绳结,里面是块黑乎乎的东西,硬得像石头。“这是我刚做培训时,老陈给我的老面引子,”
她说,“已经传了三十年了,跟着我从连锁餐厅到素味斋。等张奶奶的孙子来学做包,我就把这引子分他一半,告诉他‘这里面藏着三十年前的面香,你得好好养着,让它跟着素味斋一年年往下传’。”
众人都凑过来看那老面引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仿佛真能闻见三十年的面香。陈露忽然说:“我要把每年的桂花都收集起来,装在一个大瓷缸里,今年的压着去年的,明年的压着今年的,十年后打开,那香味能把整条街的人都引来。到时候给每个在素味斋待过的人都寄一小包,告诉他们‘素味斋的桂花还在香,等着你们回来’。”
“我要练一手好字,”
熊立雄说,“到时候给素味斋写块新招牌,‘素味斋’三个字旁边,加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让外国客人老远就知道,这里有好吃的月饼,有好听的歌,有能让人想起家的味道。”
徐涛抱着吉他弹起刚才在天台没弹完的调子,这次的旋律里多了老面引子的厚重,多了桂花缸的香甜,多了木桌子的温润,弹到动情处,他忽然唱出声:“月亮照在素味斋的窗,灶房的汤还在咕嘟响,有人在腌糖蒜,有人在揉面,有人说,这就是人间好时光……”
邢成义跟着哼,哼着哼着就想起老家的槐树,想起树下娘煮面的身影,眼眶忽然有点热。陈露低头看着玻璃罐里的石榴籽,它们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像无数个小小的未来,正等着被时光泡成蜜。
王店长望着院子里的桂花树,花瓣还在簌簌地落,落在灯笼上,落在青石板上,落在每个人的肩头。她忽然想起叶总说过的话:“做一家让人想回来的店,比做一家让人想来的店更重要。”
现在她信了,当素味斋的老面引子传了一代又一代,当桂花缸里藏着十年的香,当客人们在留言木桌上写下“我还会再来”
,这里就不只是个吃饭的地方,而是所有人心里的一块暖地,无论走多远,都惦记着回来看看。
灶房的银耳汤已经炖好了,邢成义盛了满满一碗,给每个人都分了勺。甜香在舌尖散开时,徐涛的吉他声正好落在最高处,像月光突然跳进了碗里。
“你们说,”
陈露舀着银耳,眼睛亮晶晶的,“等咱们的菜园子丰收了,是不是该办个‘素味斋丰收节’?让客人自己摘菜,自己做月饼,晚上就在院子里搭个台子,徐涛弹琴,王店长讲故事,我和熊立雄给大家分桂花糖,邢师傅掌勺做一桌子素宴,就像今天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
没人回答,但每个人都在笑。笑声混着桂花香,混着吉他声,混着银耳汤的甜,从素味斋的院子里飘出去,飘向满街的月光里。远处的路灯亮着,像串没摘完的星星,仿佛在说:别急,那些关于未来的模样,正在路上呢,就像这碗银耳汤,慢慢熬,总会越来越甜。
徐涛的吉他声还在继续,这次他唱得很轻,却像根线,把每个人的梦想都串了起来——老面引子在瓷缸里醒着,桂花在瓷缸里沉着,槐树苗在墙角长着,玻璃罐在月光里亮着,而素味斋的灯,会一直亮着,等着所有惦记着这里的人,回来赴一场关于温暖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