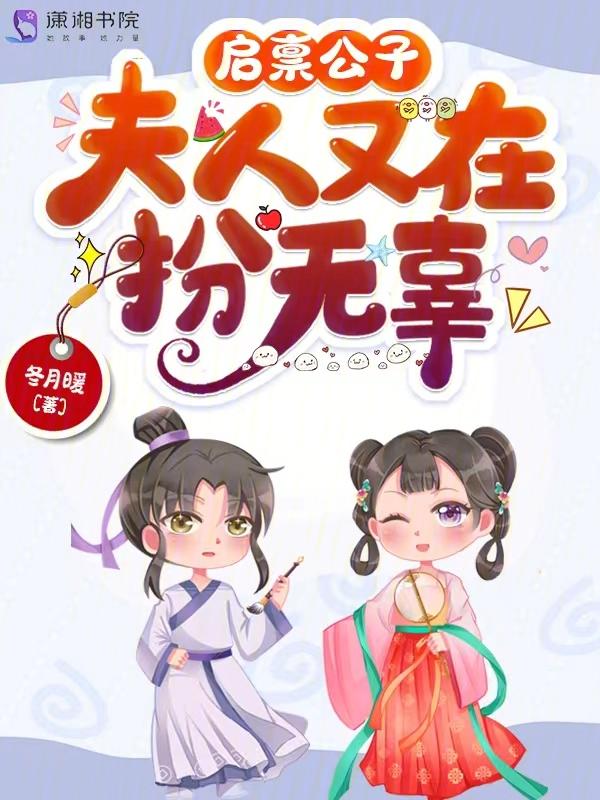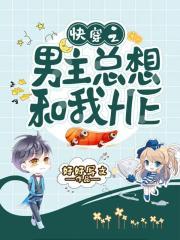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七十一章 做梦梦到未来(第2页)
第一百七十一章 做梦梦到未来(第2页)
熊立雄把糕上的红籽抠下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兜里:“我要把这些籽也埋在后院,明年长出石榴树,结的果子肯定比今年甜。到时候摘下来,一半给陈露腌石榴蜜,一半给邢师傅做石榴豆沙,剩下的留着,等金姑娘明年再来,让她带回去,种在她的国家,说不定能长出棵中国石榴树,结着两国的甜。”
陈露忽然低头笑了,肩膀轻轻抖着。“刚才想玻璃棚的时候,我还在想,要是有客人来买腌菜,说‘我爷爷当年在素味斋吃过你腌的青梅’,该多好。”
她抹了把眼角,“现在才明白,不用等那么久。你看今晚的月亮,去年照着咱们,今年还照着,明年依旧会照着。咱们在素味斋做的每块月饼,每碗茶,每句话,都像这月光,落进了谁的心里,就会在那里着光,甜很久很久。”
天台的炭火烧得正旺,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缠在一起,像棵根系交错的树。徐涛的吉他声里,多了几分暖意,仿佛已经有槐花落在琴弦上,有石榴籽滚进旋律里,有玻璃罐的咕嘟声在调子上游荡。
王店长合上牛皮本,月光在封面上淌成一条河。“走吧,”
她说,“灶房的锅里还炖着银耳汤,凉了就不好喝了。”
众人起身往楼下走,脚步踩在月光里,像踩在棉花上。邢成义走在最后,回头望了眼天台——那里的炭火还在明明灭灭,像未说完的梦。他忽然想起早上在后院看见的槐树苗,叶片上还沾着露水,在月光下闪着光,仿佛下一秒就要拔节生长,向着月亮,向着未来,向着所有关于温暖的想象。
灶房的灯亮得很暖,锅里的银耳汤咕嘟作响,像在说:这日子啊,才刚熬出甜味呢。
下了天台,素味斋的院子里还浮着桂花香,檐角的灯笼晃啊晃,把影子投在青石板上,像一群跳舞的小人。邢成义径直往灶房走,说要去看看银耳汤,刚掀开锅盖,白汽就腾地冒出来,裹着冰糖的甜香扑了满脸。
“看这稠度,再炖十分钟正好。”
他用长勺搅了搅,银耳在汤里翻卷,像朵浮在水里的云,“等会儿给张奶奶端一碗,她晚上总说口干。”
陈露正蹲在院子里收拾白天的玻璃罐,听见这话回头笑:“刚在天台上还说要研究‘音乐菜’,这会儿就惦记着张奶奶的口干了,邢师傅你这心细得跟筛面粉的箩似的。”
邢成义挠挠头,勺柄在锅沿磕了磕:“心不细哪行?去年给外国客人端月饼,有个姑娘对坚果过敏,我差点忘了王店长叮嘱的‘先问忌口’,幸好陈露你眼尖,不然麻烦就大了。”
“那是,”
熊立雄凑过来帮陈露搬罐子,罐子底在石板上蹭出“咕噜”
声,“以后咱们素味斋得挂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今日忌口提示’,邢师傅做的菜里放了什么,陈露腌的罐子里有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我还得学几句外语,什么‘花生’‘杏仁’的英文怎么说,省得外国客人比划半天咱们还猜不透。”
徐涛抱着吉他坐在门槛上,手指在弦上轻轻滑过,不成调的旋律混着灶房的蒸汽漫开来:“我那琴行也得跟上,门口摆个小黑板,写‘今日曲单’,客人来吃饭前先点歌,等菜上桌时,调子正好唱到最暖的那句。比如点了邢师傅的红糖馒头,我就弹《外婆的澎湖湾》,让甜味混着回忆一起咽下去。”
陈露忽然拍了下手,玻璃罐在怀里晃了晃:“我想到了!玻璃棚旁边得搭个小台子,徐涛弹琴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腌糖蒜,让客人看着蒜瓣在糖醋汁里慢慢变颜色。熊立雄可以切水果,把苹果雕成小兔子,把橙子片摆成月亮,邢师傅端着刚出锅的素包从旁边过,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素味斋小剧场’?”
“这主意好!”
王店长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件叠好的薄外套,往陈露肩上披,“早晚凉,别冻着。说起来,叶总前几天来电话,说他在城郊找了块地,想种片菜园,以后咱们素味斋的青菜、萝卜、桂花,都用自己种的。”
“自己种?”
熊立雄眼睛瞪得溜圆,“那我可得学种菜!小时候在老家跟着爷爷种过黄瓜,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搭架。等菜园子成了规模,我就给每颗菜挂个小牌子,写着‘这颗小白菜是熊立雄种的,炒着吃最香’,客人看见了说不定还会多夹两筷子。”
邢成义把银耳汤舀进白瓷碗,热气在碗沿凝成小水珠:“自己种的菜,炒出来带着土腥味,那才是真味。我打算在菜园边搭个土灶,客人要是想体验,就自己摘了菜来炒,我在旁边看着,教他们‘快炒要猛火,慢炖用文火’,就像当年老陈教我那样。”
“那我得在菜园里种排薄荷,”
陈露说,“夏天摘几片泡在菊花茶里,清清凉凉的。再种点玫瑰,腌玫瑰酱,抹在徐涛琴行的曲奇上,客人弹琴累了,咬一口,满嘴都是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