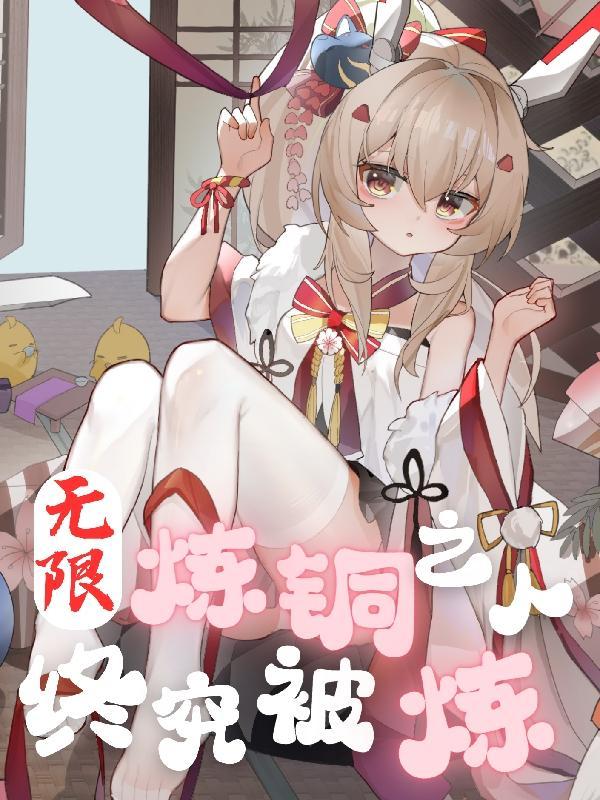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五十七章 这真的不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第1页)
第一百五十七章 这真的不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第1页)
傍晚六点的餐厅正涌着最热闹的人潮,赵大爷刚把象棋摆到老人专座,突然听见头顶“滋啦”
一声轻响——吊在半空的吊灯晃了晃,暖黄的光像被掐灭的烛火,瞬间沉入一片漆黑。
“别动!”
陈露的声音先从黑暗里浮出来,她刚在服务台核对完账单,此刻正摸索着往墙角摸,“应急灯在仓库门口,我去开!”
话音未落,就听见“咚”
的一声,像是撞到了餐桌腿,紧接着是她带着笑意的声音:“没事没事,摸着桌布呢。”
后厨的邢成义正颠着炒锅,火苗突然从灶眼灭了,锅沿的油星在黑暗里溅出细碎的光。“别开抽油烟机!”
他喊了一声,伸手摸到挂在墙上的手电筒——那是上次暴雨后特意备着的,“徐涛去拿备用蜡烛,熊立雄看看是不是总闸跳了!”
前厅已经响起细碎的笑声。有孩子在黑暗里拍手:“像在玩捉迷藏!”
赵大爷的声音紧跟着传来:“小崽子别乱跑,爷爷这儿有打火机。”
他摸出揣在兜里的打火机,“咔嗒”
一声亮起小小的火苗,橘红色的光立刻映出周围几张笑盈盈的脸,有人举着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像在捉逃跑的星光。
熊立雄在总闸箱前骂了句“这老线路”
。总闸的塑料壳烫得能焐手,他摸着墙找到绝缘手套,指尖刚碰到开关,就听见前厅传来“哇”
的一声——是陈露举着应急灯回来了,两盏应急灯在墙角投下淡绿色的光,把“老人专座”
的木牌照得像块光的玉。
“先把老人扶到应急灯底下!”
张磊的声音带着回响,他正指挥着员工把蜡烛分到各桌。小李端着烛台走过时,蜡烛被风一吹晃了晃,他立刻用手掌圈住火苗,走到赵大爷面前时,烛油已经滴了满手:“大爷您坐稳,这蜡烛是草莓味的,刚才从蛋糕房借的。”
后厨的邢成义已经摸黑支起了酒精炉。徐涛举着手电筒给他照光,光柱里飘着细小的面粉粒,像被惊动的萤火虫。“先把蒸好的馒头端出去!”
邢成义把蒸笼往案台上放,蒸汽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凉菜别碰,热菜用酒精炉温着,告诉客人稍等十分钟。”
最忙的要数传菜口。小张举着手机当灯笼,照亮递菜的手——陈露在旁边数着:“3号桌的南瓜粥,5号桌的凉拌木耳,记着报桌号时大点声!”
她的声音突然顿了顿,随即笑起来,“刚差点把醋当成酱油,幸好闻着味儿了。”
客人里有人掏出手机开了闪光灯,光柱在餐厅里织成一张亮网。有个穿西装的男人举着手机给妻子拍照,烛光在她脸上晃出柔和的轮廓,他笑着说:“比情人节的烛光晚餐还浪漫。”
妻子伸手按灭他的手机:“省点电,给服务员照路用。”
突然有人喊:“快看窗外!”
大家转头望去,应急灯的绿光里,能看见窗外的路灯亮得正稳,远处居民楼的灯光像撒在黑布上的碎钻。“就咱餐厅停电啦?”
有人笑着打趣,张磊正好端着蜡烛走过来:“说明咱这儿人气旺,电都想来凑个热闹。”
赵大爷的棋友们借着烛光摆开了棋盘。烛光在棋子上跳,老将的红漆被照得亮,走一步棋都要先用手指摸清楚格子。“你这马踩错田了!”
李大爷敲了敲棋盘,烛火晃得两人的影子在墙上歪歪扭扭,像在跳笨拙的舞。
酒精炉的蓝火苗舔着锅底,邢成义在后厨炒完最后一盘菜。徐涛举着的手电筒快没电了,光柱越来越暗,却正好照在邢成义的袖口——沾着的酱汁在光里像块亮的琥珀。“师傅,要不歇会儿?”
徐涛问,邢成义正用筷子夹起块豆腐尝咸淡,闻言头也不抬:“客人等着呢,这点黑算啥,以前在老家摸黑做饭,灶膛的火光比这亮。”
陈露端着最后一盘菜出去时,脚底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才现是个孩子举着手电筒照她的脚:“阿姨小心,这儿有台阶!”
孩子的脸在光柱里只露出半张,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陈露笑着揉了揉他的头:“谢谢你呀,小灯笼。”
突然“啪”
的一声,吊灯光线闪了闪,又灭了。众人刚“哎呀”
一声,就听见熊立雄在后厨喊:“来电啦!”
这次灯光没再晃,暖黄的光重新铺满餐厅时,所有人都愣了愣——烛光还在桌上亮着,和电灯的光混在一起,竟比平时更柔和。
“别吹蜡烛!”
赵大爷的孙女突然喊,“这样更好看!”
大家看着桌上跳动的烛火,突然都笑了。刚才摸黑找应急灯的慌张,举着手机照路的手忙脚乱,此刻都变成了相视一笑的默契——就像刚才停电时,谁也没抱怨一句,反而有人递蜡烛,有人扶老人,有人给孩子讲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