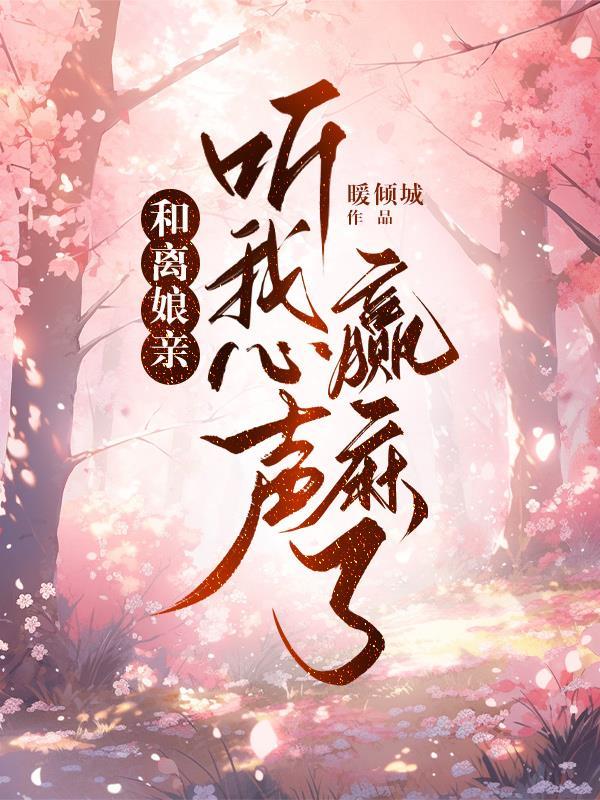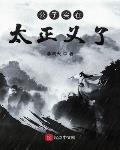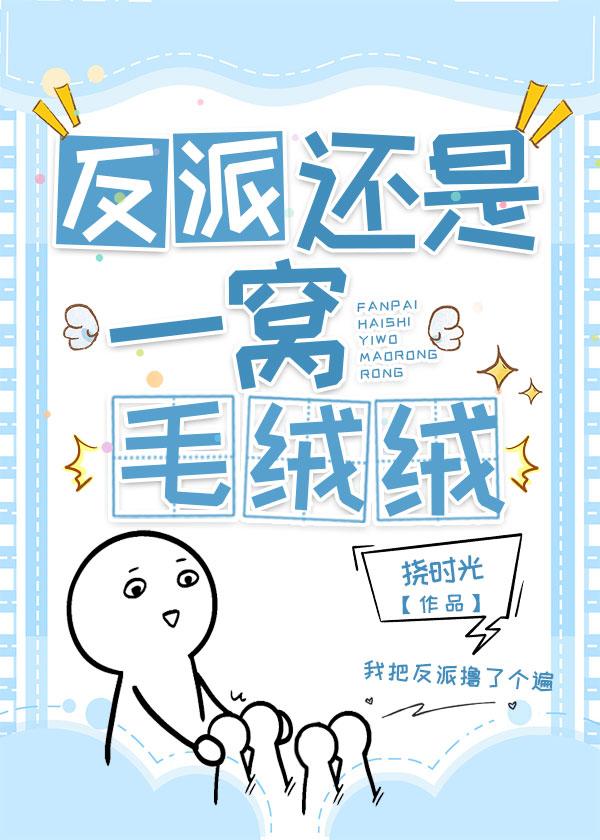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四十三章 开业前的筹备(第3页)
第一百四十三章 开业前的筹备(第3页)
,现在刀工已经稳了,土豆丝细得能透光。切到一半,他突然听见前厅传来笑声——是王经理在教服务员怎么介绍菜品。
“客人要是问‘酸儿辣女’是什么,你们就说,”
王经理清了清嗓子,学着李姐的语气,“这是咱们后厨李姐想的名,就像家里做饭,想起啥名就叫啥名,吃着也自在。”
服务员们都笑起来,有个小姑娘举手说:“那松鼠桂鱼呢?总不能说‘这是冬瓜做的’吧?”
“就说‘是张师傅雕的,比真鱼还费功夫’,”
廖总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张宣传单,“我刚去打印店加印了这个,上面写着‘所有荤菜模样,皆是素心所做’——叶总说,这才是咱们的底气。”
傍晚的时候,叶总来了。他没进后厨,先去看了前厅的布置——窗花贴在了玻璃窗上,菜牌挂在了竹架上,连老槐树底下都摆好了两张桌子,桌布是李姐用旧围裙改的,蓝布上绣着朵简单的莲花。
“不错,”
叶总摸着槐树的树干,树皮粗糙的纹路蹭着掌心,“像个能让人坐下来吃饭的地方。”
他转头看向后厨,“明天开始试营业,先请街坊邻居来尝尝,有啥不合适的,咱们再改。”
邢成义正把切好的土豆丝放进盆里,听见这话,手顿了顿。张师傅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紧张,就像平时练的那样做——当年金沙食府试营业,第一天就把醋放多了,客人说酸,我们第二天就改,现在不也成了招牌菜?”
试营业的消息传得很快。当天晚上,就有街坊来敲门,是个老太太,手里拎着袋自家种的青菜:“听说要开素斋店?我老婆子爱吃素,到时候可得给我留个座。”
李姐赶紧把老太太往屋里请,小林端出刚蒸好的八宝菠萝饭:“奶奶您尝尝!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用的是bJ的果脯。”
老太太舀了一勺,眯着眼睛说:“甜得不齁,比我孙女买的罐头好吃。”
她突然指着墙上的菜谱,“这‘团圆素丸’,能给我留两斤不?我儿子明天回来,他就爱吃这个。”
李姐赶紧记在本子上:“没问题!明天一早我就给您做,保证热乎的。”
老太太走的时候,李姐把那袋青菜留下了,说“明天做个清炒时蔬,也算您给咱们添的菜”
。邢成义看着那袋带着泥土的青菜,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就像小时候,邻居总会把刚摘的菜往家里送,说“添双筷子一起吃”
。
天黑时,大家才忙着收拾。后厨的案板擦得锃亮,蒸箱里还温着明天要用的糯米,前厅的灯亮着,像给晚归的人留的光。张师傅把明天要雕的冬瓜泡在水里,说“泡一夜更软,好下刀”
;小林把写坏的菜谱草稿攒起来,说“留着烧火,给蒸箱添点热”
;李姐把围裙洗了,晾在老槐树下,风一吹,蓝布上的莲花像在动。
邢成义最后一个离开。他锁门时,回头看了眼院子——竹架上的菜牌在风里轻轻晃,灯光透过玻璃窗,在地上投下窗格的影子,后厨的蒸箱还在出轻微的嗡鸣,像在说“别担心”
。
走在文化街的石板路上,他突然想起培训第一天,四十个人挤在金沙食府的会议室,不知道未来会去哪。而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菜谱,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老槐树,还有一群愿意等他们开业的街坊。
明天就要试营业了。邢成义摸了摸口袋里的新工牌,暖黄色的牌子在夜里像块小太阳。他知道,明天肯定会手忙脚乱,可能会把酱汁淋错,可能会忘了菜名,可能会有客人说“这冬瓜鱼不像鱼”
——但没关系,就像张师傅说的,慢慢来,家人总会等你把菜做好。
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突然想,明天一早要早点来,给老槐树浇点水,再把小林雕坏的冬瓜虾米捡起来,摆到酸儿辣女的盘子里——毕竟,家人做的菜,从来不怕不完美。
离开业还有一天,禾家素斋的烟火气,已经悄悄漫出了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