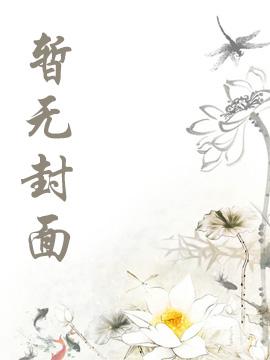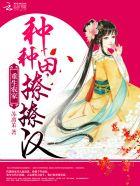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三十九章 收钱是一门手艺(第2页)
第一百三十九章 收钱是一门手艺(第2页)
她在黑板上写下“+++……+oo”
,“这是最基础的手练习,结果是oo,谁能在一分钟内算对,就算过关。”
这话刚说完,教室里就响起一片按计算器的声音,像下雨时的嗒嗒声。邢成义深吸一口气,手指刚放在按键上,突然想起张琪说的“固定动作”
,先把肘部放在桌子上,让手腕有支撑,然后从开始按。可按到的时候,他突然慌了神,把“+”
按成了“+”
,只好从头再来。
旁边的老周急得额头冒汗,手指在计算器上乱按,结果算出来个“ooo”
,自己都笑了:“这数不对啊,我记得小时候算过,没这么多。”
张琪走过来,指着他的手指说:“你看,你按的时候手指总飘,按‘’的时候碰到了‘’——就像你颠锅时手不稳,菜就会洒出来,一个道理。”
陈露算到一半突然停了,盯着计算器屏幕呆。邢成义碰了碰她的胳膊:“怎么了?”
她小声说:“我突然忘了加到几了……刚才光顾着看你怎么按了。”
两人一对视,都忍不住笑了,刚才的紧张劲儿散了不少。
张琪没催大家,自己坐在讲台边,也拿了个计算器慢慢按。她按得不快,手指起落很均匀,像在弹钢琴,等大家都停了,才抬起头:“算错了没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节奏。有人适合快节奏,像打快板;有人适合慢节奏,像拉二胡,节奏对了,自然就顺了。”
她请算得最快的小美上台演示。小美捏着计算器,手指像小鸡啄米似的,嗒嗒嗒就按完了,屏幕上跳出“oo”
,用时秒。大家刚要鼓掌,张琪却笑着说:“但她有个小问题——按到‘’的时候,手指顿了一下,说明这里有点不熟,回去多练这一段,下次能更快。”
这话让邢成义心里一动。以前学东西总想着“赶紧学会”
,却没注意“哪里学得慢”
。就像叠盘花时,他总在“卷花瓣”
那步卡壳,却从没想着单独练这一步,难怪总比别人慢。
接下来的练习,大家都学乖了——老周把总出错的“o到o”
单独摘出来练;陈露在纸上写下数字,按顺序标上记号,免得忘了加到几;邢成义则跟着张琪说的“节奏”
,慢慢按,虽然还是慢,却没再算错过。
中午休息时,张琪被一群学员围着问问题。有人问“遇到顾客说‘没找够钱’怎么办”
,有人问“手机支付没到账怎么处理”
,她都笑着回答,声音不大,却让人听得清清楚楚。邢成义远远看着,见陈露挤在人群里,手里拿着个小本子,正飞快地记着什么。
“别看了,再看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老王拍了拍他的肩膀,递过来半瓶冰红茶,“说实话,这张老师不光长得好看,讲得是真明白——我以前最怕算账,现在觉得好像也不难。”
邢成义喝了口冰红茶,冰气顺着喉咙往下走,心里却暖暖的。他现自己不再只注意张琪的样子,开始记她说话的语气——解释问题时会先说“你别急,咱们一步一步来”
;讲到容易出错的地方,会举个生活里的例子,比如“就像咱们买菜,老板多找了钱,你心里也会嘀咕是不是算错了”
。这些细节比“漂亮”
更让人觉得舒服。
下午的课是“收银实战”
。张琪在模拟餐厅里搭了个临时收银台,找来几个学员当“顾客”
,有的假装“买完单说没点这道菜”
,有的故意“用现金付账,让找零凑整”
,还有的假装“手机没网,付不了款”
。
邢成义抽到的“顾客”
是老周,老周故意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说:“小伙子,我刚点了碗面,十五块,你找我三十五——对了,我没零钱坐车,能不能找我三个十块,一个五块?”
邢成义想起张琪说的“先验钞,再问需求”
,先把五十块展开,对着光看了看(虽然是练功券,却做得很逼真),然后说:“没问题,您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