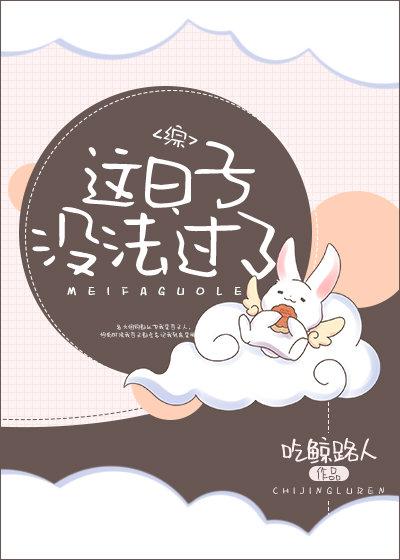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穿越隋末唐初,开局举家搬迁 > 第658章 上洛来信(第1页)
第658章 上洛来信(第1页)
三月中旬,江陵城已浸在融融春意里。江岸柳色抽新,嫩绿的柳丝在风中轻轻摇曳,桃枝初绽浅蕊,粉白的花朵星星点点地点缀其间。
城外浩荡江风裹着水汽与草木微香,悠悠地穿过高大宫墙,轻柔地拂入禁中。
萧铣迁都江陵之后,曾着力修复西梁旧制。皇家宗庙与园林皆依前朝规制重整,殿宇也在西梁旧基之上修缮而成,飞檐斗拱间尚留古意。
只是自统帅单雄信率军占据江陵、入驻皇宫以来,可不曾有过太多讲究,宫中旧日内侍、宫女多半遣散,只留寥寥数人料理杂务,偌大宫城早已不见往日繁盛气象。
殿宇依旧巍峨,檐角铜铃随风轻响,清脆的铃声在空旷的宫中回荡,却再无内侍穿梭、宫娥成行的繁闹。
连廊与阶前处处空旷冷清,各处宫道之上,闲散宫人踪迹全无,取而代之的是持戈而立的甲士。他们身姿笔挺、神色肃穆,脚步声与甲叶轻擦之音,在空寂殿宇间格外清晰。
阳光穿过高窗,洒在光洁的金砖地上,反倒衬得殿内静得落针可闻。少了宫闱原有的柔媚温软,多了兵戈占据后的沉肃与萧索,连春风拂入殿中,都似带着几分不敢张扬的轻缓。
后宫深处,瑞景殿偌大的庭院里,韩世谔挺矛而立。旋身挥击间,长矛破空之声锐响不绝。
他步法沉稳如钉,转、劈、刺、挑环环相扣,矛尖点处带起凌厉风痕,每一击都沉猛利落、劲力透锋。衣袂随动作翻飞,矛影纵横却丝毫不乱,庭院青石地面被矛风扫得微尘轻扬,连檐下垂落的柳丝都被劲气拂得频频颤动,足见其身手矫健、力道不俗。
侍立于回廊之下的亲卫副将,是跟随韩世谔多年的心腹旧部。此刻望着院中纵横驰骋的身影,眉宇间藏着几分隐忧,眼底却又翻涌着深切的追忆。
昔日战场上累伤而致性命垂危的画面犹在眼前,他一度以为主将再难提兵器、复旧勇,可此刻韩世谔矛风凌厉、步法稳健,气力与身手皆已恢复往昔水准,甚至更添几分沉猛。
副将望着那道矫健身影,既有旧疾尽愈的欣慰,又暗忧他这般奋力操练,耗力过甚,一时心绪复杂,久久未一言。
韩世谔一杆长矛骤然收势,矛尖稳稳顿在青石地面,只听“铮”
的一声轻响,劲力直透石下,微尘缓缓落定。他周身气息平稳,不见半分急促,只是额角覆了层薄汗,衣角上沾了几道尘土,更显悍厉。
回廊下的亲卫副将见状,连忙上前半步,欲言又止。
韩世谔抬手抹去下颌汗珠,瞥他一眼,声音沉朗:“跟着我这么多年,还是这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副将垂,语气里带着几分如释重负:“末将只是……没想到将军恢复得如此之快,矛法依旧如当年一般凌厉,看得末将既安心,又怕将军操之过急,伤了旧体。”
韩世谔握住长矛,指节微微用力,望向殿外春色,淡淡一笑:“你可莫要小瞧我那元正侄儿。这几年,我一直遵照他的叮嘱调养,从不敢擅自妄动。他的医术着实厉害,尤记当年初见他时,我这身子早已行将朽木,整日只想着寻一处安静之地,了此残生便是………”
副将不待他说完,已是忍不住抢着开口,语气里有些唏嘘道:“将军这话有理!当年你重病缠身,连那有名的孙老道都束手无策,直言将军顶多只剩两旬性命,谁曾想元正侄儿仅凭药浴调理、内外施针,不过一年光景,便硬生生让你日渐痊愈,如今你非但恢复往昔,甚至更胜从前,这等医术,当真称得上是起死回生!”
“那也是我侄儿,你可莫要胡乱攀附。”
韩世谔口中虽是略带斥责的话语,脸上却并无半分怒意,反倒漾起一抹温和又带着几分自得的笑意。
可话音刚落,他脸上的笑意便缓缓淡去,神色渐渐沉凝,话锋陡然一转,沉声问询道:“长宏率轻骑前去为元正侄儿复仇,至今可是已有半年之久?”
副将垂,指尖在身侧轻轻掐算片刻,略一沉吟后抬,语气凝重道:“何止半年,距刘长宏先生领命出行,至今已有近八月了。”
“也不知他们一路是否顺遂,更不知何时能有书信传回………”
韩世谔望着院中风微动的柳枝,声音轻了几分,眉宇间凝起一层掩不住的忧虑,握着长矛的手也不自觉收紧了些。
也正在此时,回廊处一名守卫脚步急促,快步穿过廊下,脸上带着几分按捺不住的欣喜,径直朝着二人躬身来报。
“禀将军,上洛来信!”
那守卫拱手行礼,手中捧着一封封了火漆的书信,声音因激动而微扬,脸上的喜色更是藏都藏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