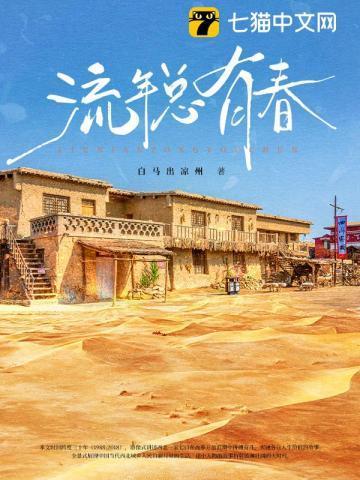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风起,云涌,雷鸣,雨重 > 第484章 火红的酒馆(第1页)
第484章 火红的酒馆(第1页)
“我需要力量,足够撑起一片干净天空的力量!若做焚世的恶魔是错,那就让我当一块垫脚石!一块铺就她重生之路的顽石!”
“哼。”
角落传来一声沉闷的嗤笑,像钝器敲击朽木。
吧台后,一直沉默擦拭酒杯的老板终于抬起了脸,昏黄的灯晕勾勒出深刻如刀凿斧削的轮廓,一双眼睛深陷在眉骨阴影里,浑浊却锐利。
粗糙的手指捏着被擦得锃亮的粗陶杯,动作稳定得如同磐石,视线在西海因激动或酒意而涨红的年轻面孔上停留片刻,里面燃烧的炽热和痛楚,似乎穿透了时光的尘埃,触动了记忆中某个同样滚烫的角落。
“战争哪有什么对错?”
老板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经历过太多铁与血洗礼后的疲惫淡漠,却又奇异地蕴含着千钧之力,随手将杯子“哐”
一声顿在吧台上,脆响在寂静的酒馆里犹如惊雷。
“上了战场的人,谁不是抱着自己认定的‘正确’在挥刀?历史书中撰写的辉煌,不过是赢家擦干净血手后,给自己脸上贴的金片子!”
酒馆老板布满厚茧的手指,敲了敲坚硬的台面,目光如鹰隼般攫住西海,浑浊的眼底骤然掠过一丝穿透性的精芒。
“你们两位大人物的道理,我不敢妄断。但有一点说的不错,在这乱世之中,想站直了说话,拳头不够硬,膝盖就得弯。”
抓起酒瓶,老板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劣质的烈酒,麦芽酵的微酸和酒精的辛辣瞬间弥漫,喉结剧烈滚动,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也仿佛烧穿了尘封的记忆。
“我在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铁十字旗在我头顶飘扬过,雄鹰的羽翼折断的声音,我也听过。”
老板放下空杯,抹了把嘴,声音沉得像浸透了的黑泥,粗粝的手指无意识划过吧台上的一道陈年刀痕,眼神变得悠远而苍凉。
“我们流的血,够把波罗的海染红几次,为了守住脚下的土,为了守住心中的神,可最后呢?”
一声嗤笑,带着刻骨的嘲弄。
“领土?割了,钱袋子?空了,连信仰都被碾碎在马蹄和弯刀之间!活下来的像野狗一样散在多瑙国那边!剩下像我这种骨头太硬的,就只能在这片废墟里,做一条守着破烂酒馆的孤魂野鬼。”
老板猛地一拳砸在吧台上,震得杯碟乱跳,眼底的苍凉瞬间化为熔岩般炽烈的愤怒,布满血丝的眼睛缓缓抬起,目光如同冰冷的铁钩,死死钩住西海,身体微微前倾,带着浓重酒气的呼吸仿佛带着铁锈味,每一个字都像从牙缝里磨出来的砂石。
“大人,您刚才说,您‘需要力量’?”
酒馆老板的嘴角扯出一个近乎狰狞的弧度,浑浊的眼珠里,被酒精和往事点燃的精光,此刻亮得骇人,“您也向往那种能砸碎枷锁、能把一切东西统统碾进泥里的力量吗?!”
“当然!”
西海猛地站了起来,酒精的晕眩混合着被目光点燃的熊熊烈火,瞬间冲垮了之前的脆弱与迷茫,站得笔直,如同一柄骤然出鞘的剑,脸颊因血气上涌而绯红,声音洪亮得震得梁上灰尘簌簌掉落,迎着如同铁砧般沉重凝视的目光,毫不退缩,眼中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
“为了我的祖国!刀山火海,在所不惜!战争或许不是唯一的道路,但绝对是必须铺设出的道路。”
“如果烈火焚林化田的手段过于危险,那我就需要一把足够大的锄头,将这片荒芜的荆棘之地,一点点开垦出来!”
“如果你拿不住这把锄头呢?”
酒馆老板的声音不高,却像铁块砸在夯实的土地上,沉闷而极具穿透力。
脸上的皱纹非但没有舒展,反而像被无形的力量拉扯,绷紧的皮肤下,虬结的肌肉虬起,青筋如老树盘根般,在紧握的双拳和小臂上搏动。
按在橡木柜台上的手,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厚实的木质台面竟出一阵呻吟般的“嘎吱”
声,仿佛下一秒就要塌陷。
然而他的嘴角却向上扯开一个极其细微的弧度,浑浊眼底翻滚着岩浆般的兴奋光芒,死死锁在西海脸上。
得一股无形,带着铁锈与血腥味的恐怖气压骤然降临,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油脂,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肺腑。
周围酒客桌上的残酒在杯壁上剧烈震颤,悬挂的油灯火焰被压得蜷缩成一点幽蓝,酒馆老板此时散出了骇人的气场,并且逐渐攀升,赫然突破了传奇境界,但西海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咬着牙,顶着足以碾碎凡骨的威压,硬生生向前踏出一步!
陈旧的地板在脚下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剧烈的压力让他太阳穴突突直跳,毛细血管在皮肤下隐隐破裂,但充血眼眸里燃烧的火焰,却愈炽烈,声音如同从胸膛里硬生生挤压出来,洪亮却带着撕裂般的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咳出的血块,
“那就用牙咬!用脚抬!就算全身骨头都被碾碎成渣,我也要用这摊烂肉!死死扛起这把锄头!”
“那如果一把锄头不够呢!”
海因里希的喝问紧随而至,如同战鼓的重锤,按在柜台上的双手猛然力,“轰隆!”
一声巨响,坚固厚重的橡木柜台如同被巨兽的利爪撕开,瞬间化作无数纷飞的木块和尖利的碎片。
木屑烟尘弥漫开来,仿佛一场微型爆炸,酒馆老板高大的身影,在弥漫的尘埃中骤然挺直,如同从废墟中拔地而起的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