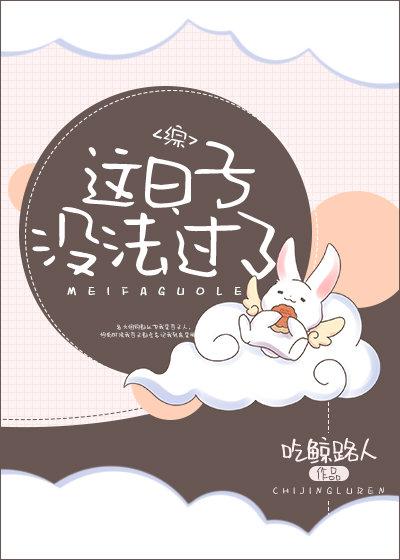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天下为聘 > 23第 23 章(第2页)
23第 23 章(第2页)
这其中深意,若非如他这般,在君王身边侍奉了数十年,早已将一颗心磨得七窍玲珑之人,又有谁能真正窥破那九重宫阙之后的帝王心术?
赵渊此书,看似体恤,实则字字皆是枷锁。这一道旨意,便等同于将太子软禁在了雍州,彻底剥夺了他回京争辩、收拾人心的机会。
当然,还有更深一层。
只要太子赵钰的储君之位一日未废,他便是悬在诸位皇子头顶最名正言顺的利剑,是朝堂党派得以暂时平衡的秤砣。若此刻太子轰然倒台,朝中必将掀起一番惨烈的恶斗,那才是陛下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帝王之道,在于制衡。
靳忠想到此处,心中对赵渊的敬畏又深了几分。
不过……无论这储君之位最终花落谁家,看陛下今日对朔津之事的雷霆之怒,郭亮那边,怕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
想到这里,靳忠的嘴角,逸出一丝几不可察的自得笑意。幸好自己多年来行事谨慎,与那郭亮虽有往来,却仅止于几句场面上的称兄道弟,从未收过他一分一毫的好处。如今他大厦将倾,自然也牵连不到自己身上。
为奴者,最要紧的便是这九个字:知进退,明得失,懂取舍。
正当他沉浸在这份独善其身的通透之中时,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那正为他浣足的小黄门,正抬着头,用一种好奇的目光偷偷打量着自己脸上那抹转瞬即逝的笑意。
靳忠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啪!”
一声清脆刺耳的响声,在寂静的掖省内炸开。
他反手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那小黄门的脸上,力道之大,直接将那瘦小的身子打得一个趔趄,滚到了一旁。
“没规矩的东西!”
靳忠的声音依旧不高,却带着一股子淬了冰的寒意。
那小黄门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得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连滚带爬地跪了回来,一边重重地磕头,一边颤声道:“奴婢该死!奴婢知罪!干爹息怒,干爹息怒!”
靳忠冷冷地看着他,缓缓将脚从铜盆中抬起。
“揣测主子心意,乃是宫中第一等的大忌。若是在御前让你这般当值,不出半炷香的功夫,你的脑袋便要与脖子分家了!”
“干爹教训的是!奴婢以后定当谨记于心,再不敢犯!”
那小黄门抬起头,半边脸颊已经高高肿起,嘴角渗出血丝,眼中却满是机敏与后怕,“奴婢一定用心学,日后好为干爹分忧。”
“哦?”
靳忠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的怒气倒消减了几分,“你倒是个机灵的。”
“奴婢这点机灵,都是平日里看干爹为人处世,耳濡目染学来的。”
这话,既是奉承,又带着几分真诚。靳忠挑了挑眉,“你叫什么名字?”
“回干爹,奴婢贱名刘振。”
“刘振……”
靳忠默念了一遍,点了点头,却没再多言,只是将脚伸向另一名早已吓得不敢动弹的小黄门,“宫里的学问,深着呢。慢慢学吧。”
“是,奴婢记下了。”
刘振恭敬地再次叩首。
靳忠对他已然失去了兴趣,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刘振和另一个小黄门如蒙大赦,不敢抬头,弓着身子,端着铜盆,碎步倒退着,快步退出了掖省。
待房门被轻轻合上,掖省之内,再次恢复了那令人窒息的安静。靳忠缓缓闭上眼睛,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只是那跳动的烛火,将他脸上那深邃的皱纹,映照得愈发晦暗不明。
*
朔津郡最大的官仓——永丰仓外。
奉旨协同查案的侍御史陆琰,一身酱紫色官袍,头戴獬豸冠,面目森冷。他与一身青金铁甲、按剑而立的彭坚并肩。在他们身后,站着百名刀剑出鞘的朔津郡兵。此兵马,监乃是监察御史陆琰凭天子节钺,自朔津郡尉府临时征调,以行“清查仓储,震慑宵小”
之权。
那朔津郡守及一众官吏也跟在一旁,噤若寒蝉。
“开仓!”
随着陆琰清冷威严的声音落下,仓储大吏战战兢兢地上前,用颤抖的手开启了那一道道厚重的门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