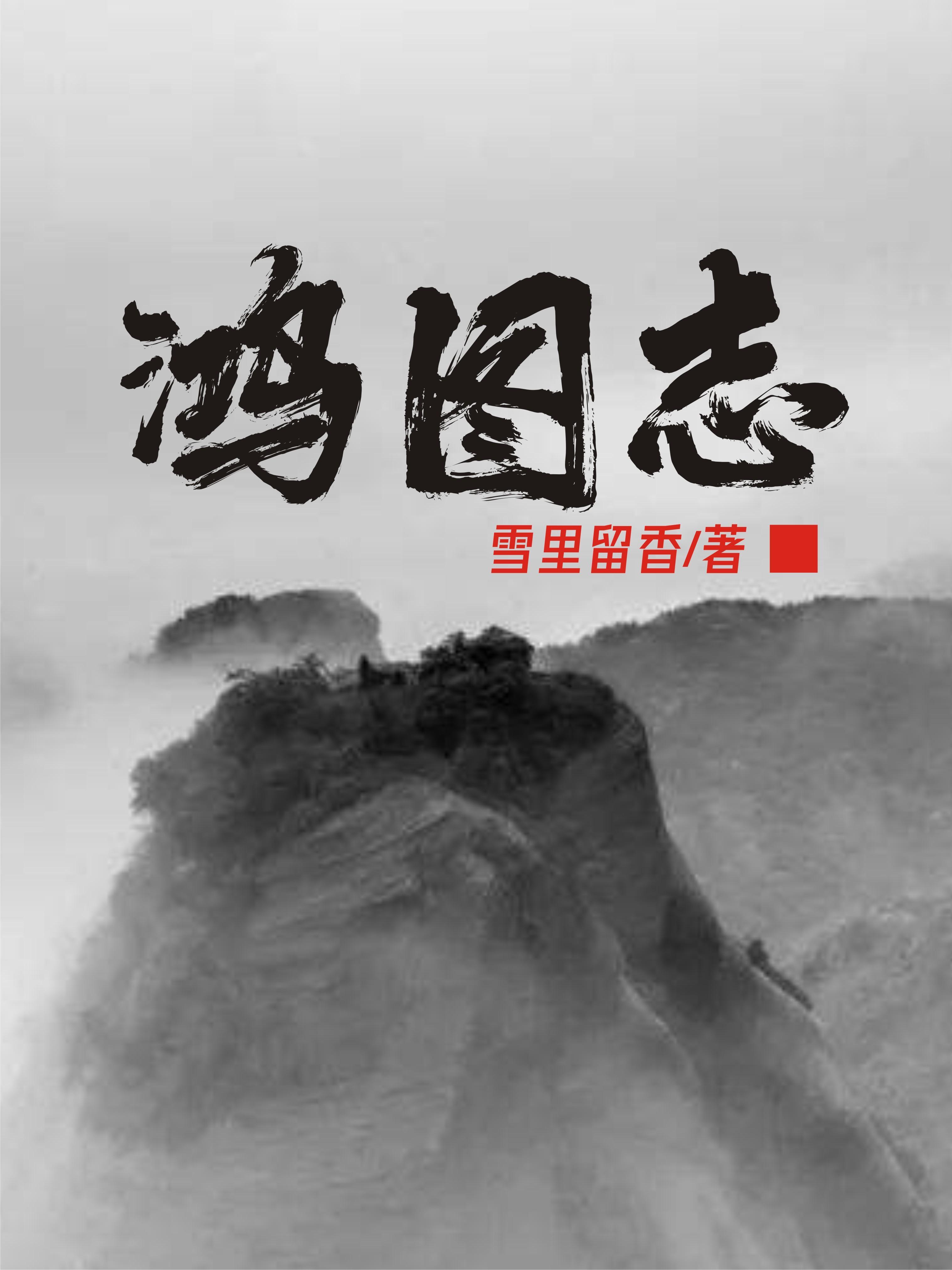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权势巅峰:分手后,我青云直上 > 第480章 赵寸光赵希言(第1页)
第480章 赵寸光赵希言(第1页)
自赵希言记事起,父亲赵广志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模糊而遥远的符号,从未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任何温暖的印记。
那时候他也不叫赵希言,而是按村里族谱的排序,取名赵寸光。
母亲孙红英是个坚韧的女人,为了养活他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咬咬牙,跟着同乡的姐妹去了遥远的南方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
爷爷奶奶年迈体弱,照看三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实在力不从心。
于是,刚上小学没多久,赵寸光就被送到了邻村山脚下的姥爷家。
姥爷是个孤寡老人,参加过那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一条腿落下了残疾,性格像山里的石头一样又冷又硬。
他话很少,眼神总是很严肃,对赵寸光这个外孙,也说不上多亲热,只是管他一日三餐,不让他冻着饿着。
童年的赵寸光是孤单的。
他没有玩伴,姥爷也不许他像别的野孩子一样满山遍野地疯跑。
大部分时间,他就待在那个光线昏暗的老屋里,唯一能接触到外界的,就是村里定期放的一些免费书籍和宣传册。
这些书大多枯燥乏味,无非是些政策解读、党史宣传、农业技术手册之类。
可就是这些在别人看来毫无趣味的文字,却成了赵寸光童年最大的慰藉和启蒙。
他囫囵吞枣地读着,许多道理似懂非懂,但那些关于国家、理想、责任的宏大叙事,却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他幼小的心田。
或许是天资尚可,也或许是别无选择只能埋头书本,赵寸光小学和初中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中考那年,他更是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这在那个偏僻的山村,算是个不小的新闻。
姥爷那张常年紧绷的脸上,也难得地露出了一丝松动,破天荒地给他做了一碗加了牛肉的面条。
就在赵寸光怀揣着对未来的朦胧期待,准备在高中继续拼搏时,一个几乎被他遗忘的人,回来了。
赵广志,他的父亲。
十几年音讯全无,再次出现时,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灰头土脸离家的穷小子,而是开着锃亮小轿车、穿着笔挺西装、口音夹杂着南方腔调的“赵老板”
。
他不是衣锦还乡、补偿家人的。
他是回来离婚的。
他在南方早已重新成家,有了新的子女,这次回来,就是要彻底斩断与过去的牵连。
母亲孙红英哭得撕心裂肺,骂他狼心狗肺。
爷爷奶奶气得浑身抖,指着鼻子让他滚。
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的赵寸光,积压了十几年的委屈、愤怒和屈辱,在这一刻如同火山般爆了。
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疯子,冲上去揪住那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的衣领,嘶吼着质问他为什么,凭什么!
回应他的,是赵广志冷漠的眼神和身边保镖毫不留情的拳脚。
他被狠狠踹倒在地,拳头和皮鞋如同雨点般落下,差点被打死。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真的要死了,耳边是母亲凄厉的哭喊和弟弟妹妹惊恐的尖叫。
最后是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和乡邻拉开了几乎失控的场面。
赵广志丢下一叠钱,算是“补偿”
和“割裂费”
,便头也不回地开车离去,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和满地的狼藉。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击垮了赵寸光。
身体上的伤很快愈合,但心里的创伤却难以弥合。
父亲的无情和暴力,家庭的破碎,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他的心头。
高中课程本就繁重,他的心却再也无法静下来。
他从优等生变成了问题学生,沉默寡言,眼神阴郁。
他看着母亲以泪洗面,看着年幼的弟弟妹妹懵懂无助,一种身为长子的巨大责任感,沉甸甸地压在了他尚未成熟的肩膀上。
成绩一落千丈。
他决定辍学,去南方打工,像母亲一样,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这个破碎的家。
“妈,我不读了,我去打工,养活你和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