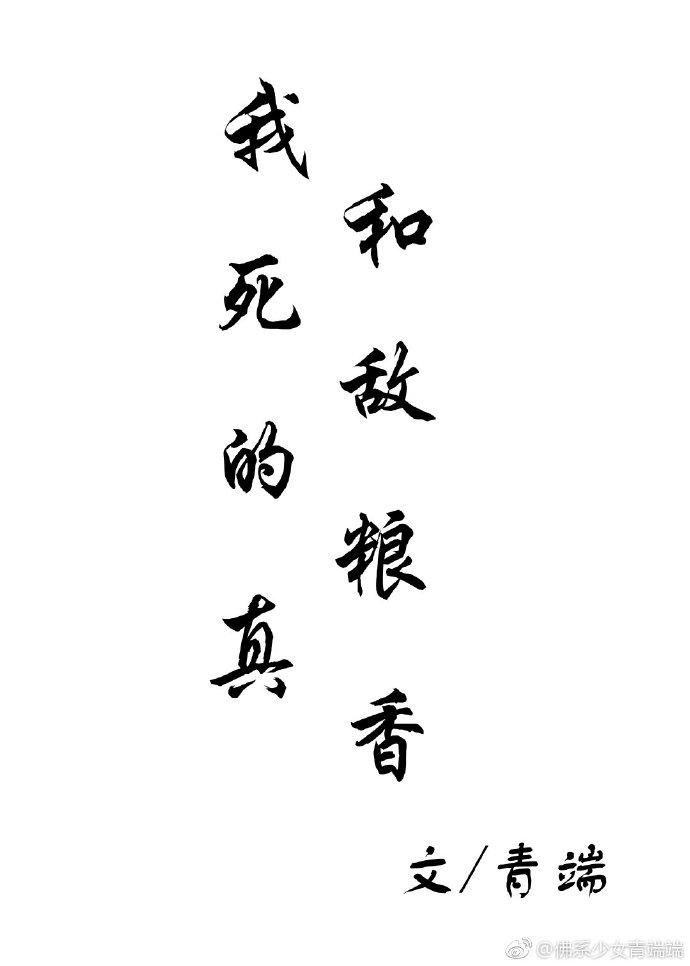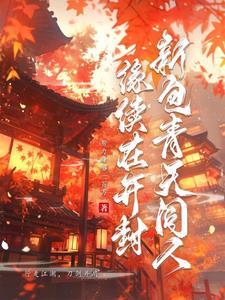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八十二章 腊八粥的暖(第2页)
第一百八十二章 腊八粥的暖(第2页)
邢成义接过碗,碗沿烫得他直换手,“这粥里我多加了颗桂圆,大爷吃着能舒坦点。”
他踩着院里的薄霜往外走,棉鞋踩在冰碴上,出“咯吱咯吱”
的响,像在给寂静的夜打拍子。
张奶奶正给老伴捶背,见邢成义进来,赶紧往炉边让,“快坐快坐,外面老冷了。”
大爷喘着气,看见碗里的粥,眼里亮了亮,“素味斋的粥就是香,白天没喝够,这会子闻着,馋虫又勾出来了。”
邢成义帮着把粥碗递过去,“陈露特意给您温的,说加了桂圆,暖身子。”
大爷小口抿着粥,红枣的甜混着桂圆的香,顺着喉咙滑下去,咳嗽竟真的轻了些。张奶奶在旁边抹泪,“你们啊,比亲儿女想得还周到。”
回到素味斋时,邢成义见王店长正翻箱倒柜找东西,竹箱里的旧布料翻得乱七八糟,蓝的、灰的、带补丁的,堆在地上像座小山。“找啥呢?”
他蹲下来帮忙理,“我记得有块红布,去年做灯笼剩下的,想给萌萌剪点窗花,明儿贴在粥桶上更喜庆。”
王店长扒开一堆蓝布,终于在箱底摸出块红绸子,边角有点磨损,可颜色依旧鲜亮,“找到了!你看这颜色,多正。”
陈露把泡围裙的水盆端到炉边,热水里加了点碱面,围裙泡在里面,粥渍慢慢化开,水变成了淡褐色。她用木槌捶打着围裙,“砰砰”
的声响在夜里传得远,像在敲小鼓。苏清沅凑过来,“我帮你捶会儿,你歇口气。”
两人轮流捶着,木槌落在布面上,溅起的水花落在炉边,很快就被烤干,留下圈淡淡的白印。
徐涛在灯下给苏清沅读报,读的是腊八节的习俗,说北方人要喝腊八粥、腌腊八蒜,南方人要吃腊八豆、煮粘米团。“原来南北方不一样啊,”
苏清沅托着下巴,“明年咱们也试试做腊八豆,给客人换换口味。”
徐涛把报纸折好,“我记下了,开春去南边的集市问问,看咋做的。”
炉子里的煤块“噼啪”
响了声,像在应和他们的话。
李萌萌趴在桌上睡着了,画本摊在旁边,最后一页画的是素味斋的夜空,星星像撒在天上的粥粒,亮晶晶的。王店长轻手轻脚走过去,给她披上件厚棉袄,棉袄上还带着灶房的烟火气。“这孩子,画了一天,累坏了。”
她低声说,眼里的笑意像炉子里的光,软软的。
后半夜,风刮得紧了,卷着院角的梅枝打在窗上,“呜呜”
的响,像谁在外面哭。邢成义起来添煤,看见灶房的门缝里透出点光,推开门,见陈露还在搓围裙,木盆里的水已经凉了,她的手泡得白。“咋还没睡?”
他拿起旁边的热水壶,往盆里兑了点热水,“水凉了,搓不动。”
陈露哈了哈手,“这围裙上的粥渍太顽固,不搓干净,明儿穿出去丢人。”
邢成义把她的手往炉边拉,“先烤烤火,明儿我帮你搓,保证比你搓得干净。”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素味斋的烟囱又冒起了烟,这次不是熬粥,是陈露在蒸粘豆包。黄米面包着红豆沙,捏成圆圆的团,放在蒸笼里,蒸汽一熏,白胖得像群小月亮。邢成义蹲在院门口劈柴,斧头落下,木柴裂开的纹路里,还能看见昨夜凝结的霜,在晨光里闪着碎光。
张奶奶挎着竹篮来了,篮子里是刚腌好的腊八蒜,绿得透亮,“给你们送蒜来了,配粘豆包吃,解甜。”
她看见蒸笼里的粘豆包,直咂嘴,“这豆包得好,暄腾腾的,一看就好吃。”
陈露掀开笼盖,热气扑得张奶奶满脸,“您尝尝,刚出锅的。”
张奶奶捏起一个,吹了吹,咬了口,红豆沙顺着嘴角流下来,“甜!真香!”
苏清沅和徐涛把昨天剩下的腊八粥装进保温桶,“今儿去给巷口的清洁工送点,他们天不亮就扫街,肯定没吃早饭。”
徐涛拎着桶,桶上的窗花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我还带了两个粘豆包,热乎的。”
两人走在巷子里,晨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两道并肩的线。
李萌萌醒来时,见画本上多了只猫,是王店长帮她补画的三花猫,正蹲在粘豆包旁边,尾巴卷着颗红豆,像在玩珠子。她拿起笔,给猫的脖子上加了个小铃铛,铃铛上写着“腊八快乐”
。院外传来三花猫的叫声,“喵呜喵呜”
的,像在催她出去画新的。
王店长坐在柜台后,看着墙上的日历,腊月初八的下面画了个小粥碗,旁边写着“粥香满巷”
。她拿起算盘,又算了遍昨天的账,这次算得格外仔细,算完把账本合上,对着窗外的晨光笑了。素味斋的腊八节还没过去呢,粘豆包的香混着腊八蒜的酸,正顺着门缝往外飘,像在告诉整条巷:日子啊,就该这么热热闹闹、甜甜蜜蜜地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