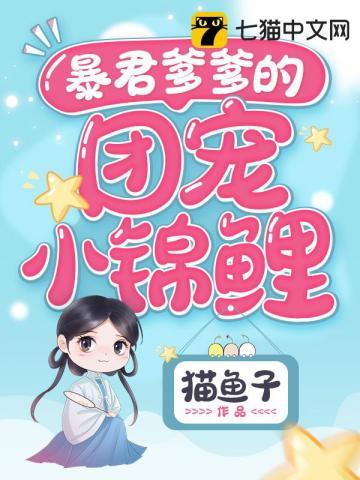爱去小说网>一生走到老 > 第一百四十八章 表哥的女朋友(第2页)
第一百四十八章 表哥的女朋友(第2页)
下午客人少的时候,大家围在槐树下“交换手艺”
。张师傅教熊立雄雕莲花,说“雕花瓣要留三分薄,像姑娘的裙摆”
;李姐教陶晨熬素高汤,说“玉米须别扔,晒干了泡茶能降血糖”
;邢成义教小林调酱汁,说“番茄酱里加勺蜂蜜,酸甜能挂在菜上”
。
小林突然想起什么,从竹筐里翻出片槐树叶:“邢哥,你看我在叶子上写的‘酸儿辣女’!”
字迹被叶脉衬得弯弯扭扭,却看得清笔画。他把叶子递给熊立雄,“熊熊哥,你传菜时要是忘了菜名,就看这个。”
“说了叫熊立雄!”
陈露伸手要抢,却被熊立雄按住手。他小心翼翼地把叶子夹进笔记本:“我得好好收着,这是小林教我的‘识字课’。”
夕阳斜照时,叶总拎着个布包进来。包里是新印的菜单,封面上印着大家的合照——张师傅举着冬瓜鱼,李姐端着米糕,邢成义和小林比着刀工,陈露和熊立雄拿着传菜盘,陶晨和李佳举着酸梅汤,每个人都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这是给常客的‘纪念菜单’,”
叶总把菜单分给大家,“每桌放一份,让他们知道,咱们这的菜不是机器做的,是这些人一刀一刀切、一勺一勺熬出来的。”
邢成义翻开菜单,看见“酸儿辣女”
下面多了行小字:“由小林切土豆,邢成义掌勺,每日限量3o份”
。他突然想起刚培训时,自己连土豆都切不匀,现在却能被写在菜单上,心里像被热汤熨过似的暖。
关门前,大家坐在槐树下数今天的“收获”
:小林的土豆丝终于没连刀了,熊立雄淋酱汁只洒了一次,李佳熬的酸梅汤被客人打包带走三瓶,张师傅教的老爷爷说“明天还来学雕虾米”
。
“我今天学会了‘微笑传菜’,”
熊立雄突然说,“陈露说客人看见笑脸,菜都能多吃两口。”
陈露踢了他一脚,却忍不住笑:“那是王经理教的,我只是转述——对了,明天我要学炒翡翠白玉汤,邢哥你得教我。”
“没问题,”
邢成义点头,“不过你得先学切菌菇,切得匀了,汤才香。”
老槐树的叶子又落了几片,飘在大家脚边。小林捡起来夹进菜单,说要做“今日书签”
。邢成义看着他认真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些忙碌的日子就像这叶子——每天落下新的,却总能在筐里攒出温暖的形状。
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他想。要教陈露切菌菇,要帮小林练转刀,要提醒熊立雄“酱汁少装半碗”
,还要给老爷爷留块最顺的胡萝卜。这些细碎的事,就像熬素高汤时慢慢渗出的鲜味,不用刻意,却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熬成了“家”
的味道。
晚风里飘来远处的饭菜香,邢成义锁上门,听见身后传来小林的声音:“明天见啊,大家!”
“明天见!”
回应声在文化街里荡开,混着槐树叶的沙沙声,像在说——日子还长,我们慢慢学,慢慢过。
禾家素斋的意外访客:餐桌旁的认亲小插曲
上午十点的后厨刚歇下来一阵。酸儿辣女的土豆丝备好了大半筐,张师傅雕的冬瓜鱼已经摆在展台上,李姐正把新蒸的桂花米糕往竹篮里装——这是给早到的客人准备的茶点,竹篮还是王经理从南门店带来的老物件,边缘磨得亮,却透着股温厚的劲儿。
“邢哥,吃饭去不?”
小林擦着手从操作间出来,围裙上沾着点糯米粉,“今天李姐做了艾草素包,还热了酸梅汤。”
邢成义把最后一把香菜理好,直起身捶了捶腰。一上午炒了八份翡翠白玉汤,切了十五斤土豆,手腕有点酸,听见“艾草素包”
四个字,肚子突然“咕噜”
叫了一声。“走,去前厅吃,那边通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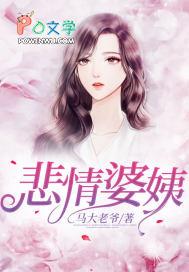
![(综同人)[综]斑的姐姐是英灵+番外](/img/273814.jpg)